我和樸學大師胡樸安先生為忘年交,我始終以前輩禮對待他,他老人家和我無話不談。可是他生長於安徽涇縣的龍坦屯,屯在萬山圍繞中,北面倚山,前臨溪水,正是個好所在。辛亥革命前,即來上海,已歷數十寒暑,但「鄉音未改鬢毛衰」,還是滿口涇縣的土話,他雖無話不談,可是我有些話不甚懂得,在瞭解上未免打了個折扣。
他生於前清光緒四年戊寅九月十三日,卒於一九四六年丙戌五月二十一日,恰值古稀之歲。和他相交而存世的殊罕其人,那麼記敘他的往事,有捨我其誰之歎了。
我涉筆人物掌故,成為習慣,編著《南社叢談》即有《南社社友事略》,凡一百七十餘人。樸安,當然是其中之一。惜乎尚不夠詳贍,最近袁君義勤借給我《樸學齋叢書》之一《五九之我》一冊,那是胡家斥資所印,屬於非賣品,印數寥寥。經過浩劫,這種作品,難以看到的了。這所謂《五九之我》那是樸安於一九三七年所作,這年為他五十九歲,盡八個月的精力,寫成了這書。他自己說:「用極誠懇的態度,極普通的文字,使前塵夢影,一幅一幅從腦中經過,而留之於紙上,使它日尋夢時,不至渺渺茫茫,毫無依據。」那書就是等於自傳或回憶錄,展閱之餘,更能充實我的寫作資料,這是應當向袁君表示謝意的。
從來樸學家,無不威儀棣棣,文質彬彬,埋首故紙堆中,作探賾索隱之舉。樸安卻不是這個類型,他亦莊亦諧、亦狂亦狷,饒有趣味性和生活氣,這是我樂於為他下筆的。
他寓居滬上,而家鄉觀念很重,留有家鄉照片數十幀,編刊《樸學齋叢書》,把照片製版登載卷首,且做了《思故鄉歌》。如云:「不禁思起我之故鄉,兒時游釣不能忘。不禁思起我之故鄉,天涯煙水勞相望。不禁思起我之故鄉,往事回頭半渺茫。窗前明月,屋角斜陽,至今可是乃無恙?」這歌渾成自然,幾近天籟。他的弱弟寄塵,著有《江屯集》《福履理路詩抄》,為南社著名詩人,且能譯述西洋詩為絕律近體,不失原作的神理和韻味,尤為難能。而寄塵之詩,實為樸安所授,其成就竟超過樸安,真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樸安談他的幼年事,節錄一二於下:「性強硬,仆跌非破皮流血不哭。好與群兒鬥,斗必求勝,不勝則視為大恥辱。入門館讀書,館師六十餘歲,精力已衰,學規極其散漫,學童日以演戲為樂。我年事雖小,而喜扮強盜,二三尺之高,翩然而上,三四尺之遠,翩然而越。後易一館師,凡到館最早者,是日背書有優先權。我每為到館之第一人,彼此互相爭早,天微明,群兒聚館門而俟,我每由後門越牆而入,故群童皆不如我之早,蓋得力於做強盜。一日,與群兒鬥,糾結不可解,我兄伯春奉母命呼我,且斥責我,我不服,轉而斗伯春,伯春長我三歲,身高於我,而斗則屈我下。我以足蹴伯春,伯春仆地,石破其顱而流血。我駭極而逃,時已薄暮,冥色四合,我家雇工,恐我迷路,自後追之,約一里餘,前臨一澗,寬可五尺,水流甚急,我一躍而過,雇工力不勝,對澗大呼,旁觀笑之,謂:三十歲男壯丁,反不及十歲孩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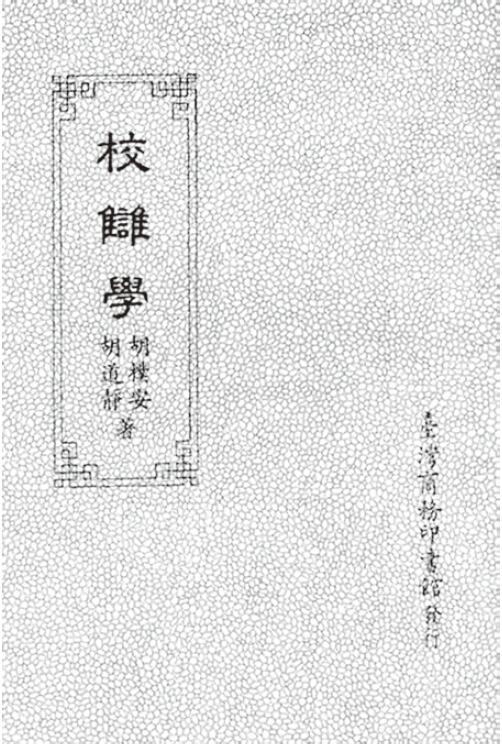
胡樸安與人合著《校讎學》
他好武,家中有一貯藏雜物之樓,因沒有人去,把梯子撤掉,他就瞞著家人,用沙袋懸於中梁,便緣柱上下,讀書之暇輒擊沙袋,以練身手。又縛小鐵條於脛足間,以練超躍。受創不出聲,家人始終沒有知道。他的同學王某,拳學少林派,那是淵源於家學的。他向王學習,從基本功著手,兩腳為騎馬式,如膝要屈,腿要平,腰要直,頭要頂,兩手握拳等,動作甚多,而以快與巧取勝;那開合虛實之勢,攻擊防禦之法,得其要領。從陳微明學太極拳,微明為陳蒼虯詩人之弟,也有詩文集行世,且能文能武,尤為傑出。樸安的拳法,因此才歸正宗。記得有一年,他得意的女弟子陳乃文,邀諸友好及老師為聯歡會,我也在被邀之列。樸安興至,在中庭一試身手。他的另一位女弟子王燦芝(秋瑾女俠之女)舞劍,這印象迄今猶留我腦際。既而樸安伸著頸項,叫我用手盡力叉著,經他一挺,我力竭倒退,為之驚歎。
樸安讀書,從過四位蒙師。年十五,他的父親自設門館,伯春和樸安,均趨庭受教。所教面很廣,「四書」「五經」、古文古詩,以及子史等等,又鬧了個笑話。原來他讀「綱鑒」至漢高祖溺儒冠,他心竊慕之,乃潛取同學之帽,承之以溺,同學訴之於師,他的父親也大加譴責,並詔以前哲「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謂:「溺儒冠當在不善須改之列,怎能學習呢!」他問:「漢高祖起兵討秦可笑嗎?」父答以:「果有秦始皇,自當討伐。」越日,問諸同學:「今日有沒有秦始皇?」有一頑皮同學,立出來說:「我就是秦始皇。」他把這同學猛打一拳,幾至流血。說是:「暴秦給我討伐過了。」
他喜讀韓昌黎的文章,敬慕昌黎之為人,韓文中之《原道》和《諫佛骨表》他讀得滾瓜爛熟。這兩篇都是闢佛的,所以他也是重儒輕釋了。一天,有一和尚,手持木魚,盤坐募化,口喃喃誦「南無阿彌陀佛」,他更提高嗓子讀《原道》,結果和尚只得避去。他父設帳之家,頗有藏書,他時常發篋翻閱,注意雜書等類,深恐父親阻止,偷偷地以油燈照讀,燈光如豆,復以黑布蒙其三面,不使光線射至父室,一次夜深假寐,幾肇焚如之禍。雜書中,最喜看尤西堂的遊戲文,袁子才的散文,以及《幽夢影》《板橋雜記》等書,既而發篋,得《九數通考》及《梅氏叢書》,為了好奇,轉治算學,無人指示,冥索默求,乃悟我國的四元即西方的代數。復發篋,得《朱子大全》《近思錄》涉獵了理學方面,影響了他,從此言語行動一變而為恂恂儒雅了。他赴郡試,購得《農政全書》《紀效新書》,又讀而好之。族人某贈他《齊民四術》,一夕閱畢,於是自詡為知兵農水火之學。既明新學之為用,研究《泰西新史》《格物入門》《格致彙編》《化學初階》等書不離手。後好文字學,對於《說文解字》,他具有別解,認為須加修改。若干年,在蕪湖萬頃墟任開墾,時劉申叔於安徽公學執教,陳仲甫寓科學圖書館,辦《白話報》,二人都精於文字學,他頗得切磋之益。
上海有國學保存會所設之藏書樓,樸安常去看書,得識陳佩忍、諸貞壯、高天梅、蘇曼殊、朱少屏諸人,均籍隸南社,他有一段自述,如云:「曼殊性疏散,其於人似有意,似無意。貞壯為張季直之得意門生,與我輩之草澤文人,其思想與行徑,似乎稍有不同。少屏當時忙於社會之事。蹤跡較密者,佩忍、天梅二人而已。二人皆好飲酒,皆好作詩,尤喜醉後發狂言。我之酒量,或過於二人,詩雖不逮,亦勉強可以追隨,因佩忍、天梅而認識柳亞子,遂加入南社。南社為文字鼓吹革命之機關,與日本東京之同盟會,遙遙相應。初由柳亞子、高天梅、陳佩忍三人發起,開成立會於蘇州之虎丘,我之加入南社也,則在成立之第二年。我加入後,我弟寄塵亦加入。南社同人好為慷慨激昂之詩人,以意氣相交結,與我之個性頗相近。」他也多藏書,自云:「好買書,每月買書之費,有時超過生活費兩倍以上。我之積書,始於民國紀元前五年,以後年有增加,苟生活費有餘款,皆用以買書,至於今日,積書在五萬冊以上,蓋已有三十餘年之歷史也。」他晚年和管際安、童心安,合築屋舍於滬西延平路,以三人名中,均有一安字,便榜之為「安居」。這兒我是常去的,書櫥、書架、書箱,可謂滿坑滿谷,總之,除坐臥一席外,余皆置書,以我估計,遠遠超過五萬冊了。但他所置的書,都屬於實用的,從不講究版本。他說:「矜宋詡明,非我輩寒士力所能及,我不勉為之也。」他讀書逢到疑難,不憚查檢之煩,非得其要領不可。因此,他常對學生說:「遇不認識之字,不要即問先生,翻過數種字典而猶不得其解,然後再問,因查書極有益於學問。」
《美術叢書》為一巨著,初為線裝本,分若干集,後改為精裝本二十冊,配一木櫃,甚為美觀。那是鄧秋枚所創的神州國光社出版的。第一集即樸安所編,第二、三集,秋枚自編,四集以後,始由黃賓虹編。又《國粹學報》,也是秋枚所創辦,復出《國粹叢書》,樸安撰《吾炙集小傳》,收入其中,末附秋枚一跋,卻有「與胡生韞玉同輯小傳」云云。樸安大不以為然,謂:「韞玉是我之名,現已廢棄不用。胡生之稱,系先生對於弟子所用者,我與秋枚,不過老闆與夥計之關係,秋枚是文字資本家,我是文字勞力者,此不可不一言以辨正。」當時國粹同人,有章太炎、劉申叔、黃晦聞、陳佩忍、李審言、黃賓虹等。羅振玉、王國維、廖季平,則經常為《國粹》撰稿。他對於以上諸子,略有評論,謂:「太炎、申叔,深於乾嘉諸儒之學,申叔之精,雖不及太炎,而博或過之。惟太炎不信甲骨文,亦不重視金石文,治學方法,不能辟一條新路。吾友程善之常為余言,申叔諸著作,多數取諸其祖與父之舊稿,此言我不能證實,但善之亦非妄言者。晦聞深於史學與詩學,而詩學出史學之上。佩忍熟於掌故,而文極條達,詩詞慷慨可誦。審言熟於選學,駢體文又極謹嚴,自謂勝於汪容甫。且箋注之學,近世殆無出其右者。賓虹深於篆刻書畫,而畫尤精,出入宋元間,不作明人以後筆法。鑒別之眼力尤高,近世之作山水者,推為巨擘。羅振玉在甲骨文上,有傳佈之功。王國維治學方法,似乎在太炎之上,更非羅氏所可及。友人某君常為我言,自王國維死後,羅氏發表之著作頗少,其言亦深可味。四川廖季平,考據極精,申叔盛稱其《六書舊義》,廖氏本班固四象之說,注重形事意義四事,頗新奇可喜,在我做的《中國文字學史》上已稍論之。」所論殊精當,可作學術參考,又見清末民初儒林之盛況。而樸安多方面獲得高榷切磋,尤為難得。
樸安從事新聞事業,始於《民立報》,該報為於右任所創辦,繼《民呼報》《民吁報》而為民國發祥的報刊。他主編小品文章,搜集明遺民之事跡與其言論含有種族思想者,編為筆記類,次第載之報端。又編有《發史》一種,凡清初不肯剃髮而被殺,或祝發而為僧者,悉為編入。又編《漢人不服滿人表》一種,自江上之師,至黃花岡止。又作小說《混沌國》,描寫清廷的腐敗情況。但此等鼓吹革命的文稿,都散失掉了。惟《發史》序,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卻引有一段,樸安錄以存之。那為《民立報》撰社論的,有宋漁父、范鴻軒、景耀月、王印川、徐血兒。撰小說的有老談,即談善吾。繪畫的有錢病鶴(後改為雲鶴),亦人才濟濟。此後瞿紹伊主辦《春申報》,招樸安為襄助編輯,為時不久,報即停刊。繼進《新聞報》,任小品編輯,乃純粹的遊戲文章。辛亥革命後,他在遊戲文章中譏誚遺老,觸犯股東的忌諱,他便辭職而去。
他認識葉楚傖,很有趣。那時,他和陳佩忍,同飲於滬市言茂源酒肆,佩忍忽對他說:「我有一好朋友,是汕頭《大風報》的主筆,新從汕頭來滬,不可不去一看。」他詢問何人,佩忍不語,久之則云:「現且不言,看到時再講。」酒罷,同到一客棧,佩忍帶領而入,便見一狀頗魁梧者,正在閱書,客至,釋卷而起。他疑心是廣東人,或是北方人,正要請教時,佩忍忽謂:「你們二位,暫不通姓名,談了話再說。」他聽對方講的是吳儂軟語;疑團更甚,沒有談到幾句話,就提到飲酒,三人便同赴酒家,其人縱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又雜談詩文,三人頹然各有醉意,彼此竟未通姓名而別。事後,樸安才知其人乃吳江葉楚傖。民元之際,姚雨平辦《太平洋報》,楚傖任總編輯,朱少屏任經理,柳亞子編文藝,兼電報版,樸安作社論與編新聞。一日,亞子以第五集《南社叢刻》謄寫稿(各地社友寄來詩文詞稿,紙張不一,寫體亦不一,均由亞子全部抄錄,錄入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三十字的紅格紙裡去,然後付印),托樸安交付印刷所,樸安粗枝大葉,不知怎樣把全部謄寫稿丟失了。亞子大發脾氣,要樸安賠償,這怎麼辦呢?結果,亞子所兼電報版,由樸安代庖,亞子騰出時間來重作抄胥,才得解決。在這時,樸安又認識了余天遂、姚鵷雛、李叔同、夏光宇,都是該報的同事。《太平洋報》費絀停止,樸安為《中國民報》作社評,又認識了鄧孟碩、汪子實、陳無我、管際安、劉民畏。他的社評往往不標題目,認為標題目麻煩,寫成了社評,就算了事,什九由汪子實代標。有一次,汪氏亦覺得標不出適當的題目,竟標之為「無題」,傳為笑柄。此後,樸安又任《民權報》編輯,時戴季陶主筆政,署名天仇,而天仇性躁急,動輒忤人,樸安對他說:「請你把天仇二字改為人仇吧!」
有關樸安的趣事很多,足資談助。他和馬君武對局為圍棋,君武下子輒悔,止之不可。他想出一抵制辦法,君武悔一子,他也悔一子,君武再悔一子,他也再悔一子,往往兩人各悔一二十子,致全局錯亂,只得通盤重下。他常和南社的朋友赴酒店醵飲。某次,隔座猜拳,喧呶不息,又復胡琴清唱之聲雜起,他很厭惡,便和朋好以巨大的聲音效之,五魁八仙,超出其上。當時以樸安的嗓子為最宏亮,大家把他的名字上加上四個形容字,為英英皇皇的胡樸安,更擴充為吞吞吐吐的朱少屏,謂其講話不爽快。期期艾艾的柳亞子,謂其口吃。圈圈點點的呂天民,謂其面有痘斑。闊闊氣氣的汪兆銘,謂其經常乘馬車。嬌嬌滴滴的葉楚傖,謂其作小說題名為小鳳。陪陪坐坐的陶小柳,謂其不善飲而侍坐。輕輕巧巧的胡寄塵,謂其出言吐語,聲音極低。馬馬虎虎的姚鵷雛,謂其行為脫略。鵷雛之不羈,確有不同尋常處。一日鵷雛乘馬車來訪樸安,其時乘馬車的都是闊人,新聞記者是沒資格坐的。及下車卻為鵷雛,樸安急詢其:「有何要事?」鵷雛說:「向你借錢。」問:「借若干?」答:「借四元。」問作何用,答付馬車錢。樸安為之大笑。一天,他赴友人酒食之約,途中遇見蘇和尚曼殊,他問:「和尚哪裡去?」曼殊說:「赴友飲。」反問:「何往?」他答:「也赴友飲。」曼殊欣然說:「那麼我們同行吧!」到即恣啖,亦不問主人為誰。實則樸安之友,並未招曼殊,招曼殊者另有其人,是兩不相涉的。南社每次雅集,觥籌交錯之餘,例招攝影師來,攝一集體照,諸社友雁行而立,呈現著溫文爾雅的氣派。某次雅集,攝集體照外,樸安赤膊別攝一騰挪超縱的拳法小影,以留紀念。
他對於事物,頗有獨特之見,常謂:「男女進而為夫婦,當注重於情之一字,不可專注重於愛之一字,愛則日久而消,情則日久而積。我覺得對於家庭,對於朋友,對於國家,惟有一情字,始能有真正的愛。」他看到舊社會嗜學者少,溺於惡習者多,發著感慨說:「近年以來,中人以上,不鬥牌者十無一人,不閱庸俗小說者,百無一人,作詩填詞者,千無一人,習經讀史者,萬無一人,躬行實踐,為身心性命之學者,曠世無一人也。」又談到吃飯問題:「中國一千人中,五百人吃飯不做事,四百九十九人,為吃飯而做事,不知可有一人為做事而吃飯?吃飯不做事者,倚賴人為生活,禽獸不若也。為吃飯而做事者,禽獸以爪牙覓食,人以知識覓食,覓食之方法不同,而其覓食則一,禽獸類也。為做事而吃飯者,具有人格,出於禽獸之上,始得謂之人。」他又說:「不能在最低等的生活立得住腳,將來決不能任大事。」
他先娶唐淑貞,體羸弱,沾時疫幾殆,後患貧血症,不治死。繼娶朱昭,樸安教之讀書,知文翰。有時樸安向國學保存會借來孤本書,朱夫人為之手抄,纍纍列於櫥架,樸安引以為樂。子女有道彥、道彰、道彤、平、泌、泠、沄。那馳譽國際的道靜,是他的侄子。平名淵,為首辟黃山許世英的兒媳,擅書畫,中年夭折,樸安很為傷痛。長子道彥早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留學美國,從事鐵路機車設計研究。一九四八年去台灣。近三年來,斥資重印其父樸安的《樸學齋叢書》,共分為三集,第一集,收入胡氏先人胡樸安、胡懷琛(寄塵)的詩文遺著;第二集,收入樸安學術著作十餘種;第三集,乃懷琛的學術著作及現尚健存的道靜作品。送給大陸諸親友和圖書館。又《俗語典》,那是樸安主持下,由夫人朱昭,前室所生之女樸平,其弟懷琛,侄道吉、道和協作編輯而成。一九八三年,上海書店為之複印,有楊樹達序、懷琛序,及樸安自序。例言最後有那麼幾句話:「本書告竣時,於各書中續得俗語,又有一千餘條,原擬附本書之後為補遺,嗣思俗語尚多,再事搜集,或可與本書相並,或竟多於本書,附為補遺,未足盡俗語之大觀,因先出此編,以饗閱者,續編嗣出。」這個續編,未見刊行,今不知原稿尚存與否了。據我所知,樸安別有兩種作品,神龍見首不見尾,成為遺憾。一《病廢閉門記》,那是一九三九年忽患腦溢血,瀕危得救,但半身不遂,自號半邊翁。他初頗抑悶,既而以易理禪理,自靜其心,謂:「譬如被判無期徒刑,不作出獄之想,獄中生活,亦頗自適。」撰《病廢閉門記》二十萬言,給錢芥塵刊諸《大眾雜誌》,逐期披羅,奈《大眾雜誌》出了若干期,便告停刊,余稿很多,存芥塵處。當時芥塵一度宣言:「倘有人為刊全書,當無條件奉贈。」可是那時紙張難購,印工昂貴,沒有人接受,今則芥塵逝世,也就下落不明。又《南社詩話》,初登《小說月報》(聯華廣告公司所發行)上,登了數期,樸安輟筆。這時,我為《永安月刊》編委之一,因商懇樸安,續撰刊諸《永安月刊》,樸安命筆寄惠,大約連登了若干期。有一次,《詩話》續稿被編輯部不慎遺失,樸安是沒留底稿的,便覺興趣索然,中斷不續了。
最近,新出《中國文學家辭典》,列入胡樸安小傳,謂:「原名胡有忭,學名韞玉,字仲明,後改字樸安。一九一六年,任交通部秘書,後任福建省巡閱使署秘書,京滬、滬杭甬兩路管理局編查課長,兼上海國民大學及持志大學國文系主任。一九二二年,著《中國全國風俗志》。一九三○年,任考試院專門委員,同年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一九三二年辭職,主持《民國日報》筆政。一九三九年,患病居家,專心著述,所寫《周易古史觀》《莊子章義》《儒道墨學說》《中庸新解》等書,均有獨到見解,成一家言。他的《中國文字學史》《中國訓詁學史》《文字學ABC》《文字學研究法》《六書淺說》《古文字學》等專著,也很有影響。其他尚有《周秦諸子學說》《儒家修養法》《文字學討論》《中國學術史》等數十種。抗戰初期,任上海正論社社長,上海淪陷後,閉門著述。抗戰勝利後,任上海通志館館長,及《民國日報》社長。一九四七年,因肝癌逝世。」他的經歷和著述,足補我文之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