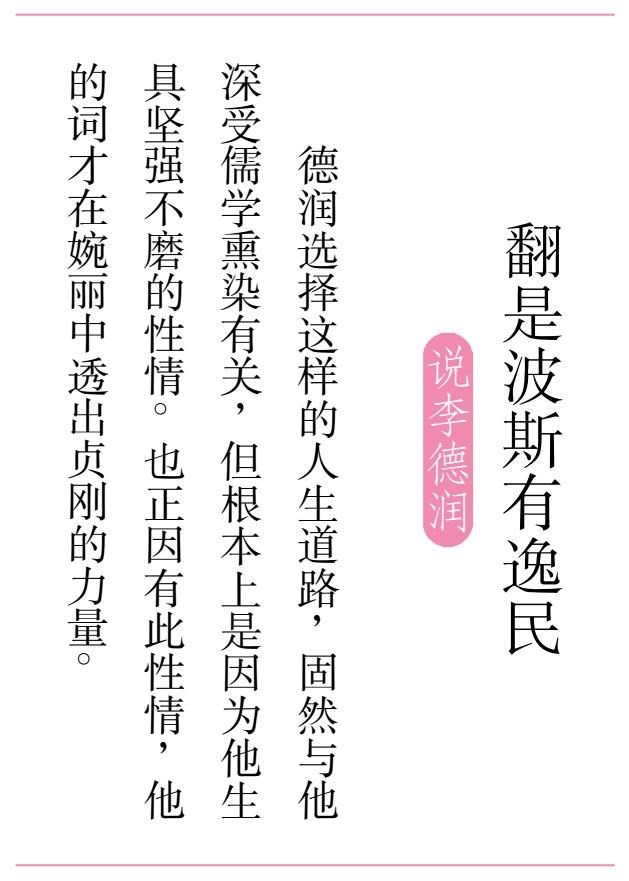

花間詞人三大家,一般指溫庭筠、韋莊、孫光憲,李冰若先生和我的太老師朱庸齋先生則認為,溫、韋而外,僅李珣 有獨特風格。
按照明人胡應麟的觀點,大家是「 具范兼鎔 」,名家則是「 偏精獨詣」,但也有諸體俱工而不免名家,如王維;在某一體裁上微有短板,卻不失名家的,如李、杜。以具范兼鎔 論,孫光憲的詞風固然非常獨特,時有警句,但風格不夠渾成,與溫、韋並列,恐怕還有未當。而若論情感的濃摯,只能溫、韋並稱,堪比崑崙泰岱,其餘只能算名山而已。在諸名家中,我偏愛李珣的詞。
李珣 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從血統上說,他並非中原人氏,而是波斯人的後代。但他生於中國、長於中國,接受儒家文化,最後成為五代時期一位罕見的有士大夫氣節的詞人。
李珣 字德潤,出生在梓州。他的先祖是唐敬宗時波斯商人李蘇沙。唐敬宗喜歡大興土木,建造宮室,李蘇沙曾獻上了罕見的沉香木材。李蘇沙後來一直生活在中國,大概也與中國人通婚,傳到德潤這一輩,有一個哥哥李玹 ,字廷儀,還有妹妹李舜弦,被前蜀的後主王衍納為昭儀。
德潤雖身膺外戚,但並沒有靠這層關係攀龍附鳳做大官,因為《花間集》僅僅把德潤叫作李秀才,或者叫作賓貢。所謂賓貢就是地方政府聽說某人很有才幹,於是具名推薦到中央去,讓朝廷來考核是不是有資格當官,到了朝廷會受到上賓一樣的接待,所以叫作賓貢。另外據宋代《茅亭客話》記載,德潤「 所吟詩往往動人。國亡不仕,詞多感慨之音」。他在前蜀被滅後,甘願做遺民,其詞就有很多感慨興亡之作。
近代中國人,受進化論和唯物論的影響,不吝用保守、反動等惡謚加諸忠於前朝的遺民頭上。但在古代並不如此。司馬遷著《史記》,列傳中第一篇就是《伯夷列傳》,讚美不食周粟的殷商遺民伯夷、叔齊。選擇做遺民,不僅是讀書人的氣節,有時還是一種鮮明的文化立場。比如宋、明的遺民,他們所守望的,不僅是內心的道德律令,還是歷劫猶存的中華文化。
德潤是給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去做遺民呢?不妨來看一看宋代詩人張詠的《悼蜀詩》,是他到蜀地做官後寫的。詩中首先說蜀地的風土人情:「蜀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奢僭極珠貝,狂佚務娛樂。」蜀地很富庶,老百姓很有錢,但風俗浮靡澆薄,就是追求虛榮,人情淡漠,不淳厚樸實的意思。大家爭相買奢侈品,花錢無度,成天不幹正事,就想著去娛樂。那麼前蜀、後蜀的統治者又是什麼樣子呢?「 當時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風復儉約。」當時主政的人沒有想過要救民瘡痍,他們不能夠讓風俗變淳,讓德化施行,讓不好的風氣轉移掉,恢復到勤儉節約的正常的風俗當中去。至於一般當官的,「情性非直方,多為聲色著」。他們的性情本來就不是很正直方正,一天到晚想的是聲色犬馬。「從欲竊虛譽,隨性縱貪攫。」任憑慾望支配本能,竊取他們不配得到的名譽,放縱自己的性情去掠奪。「蠶食生靈肌,作威恣暴虐。」像蠶一樣去一點點噬食老百姓的肌肉,作威作福,肆意地施行暴虐的政令。「佞罔天子聽( ti ng) ,所利唯剝削。」這些善於逢迎拍馬的佞人,把皇帝的耳朵都閉塞住了,整天想的是對老百姓剝皮削骨。這是德潤所仕之國。
然則他所侍奉的君主又是什麼樣的人呢?在晚唐之時,川南節度使王建利用自己手中的兵權,以及軍閥混戰、藩鎮割據的大勢,把蜀地淹為己有,建立了蜀國。後來蜀地被後唐給滅掉,復有人建立新蜀國,史稱前蜀後蜀,前蜀是王氏,後蜀是孟氏。王建原先也算英明神武,但他年老昏聵,寵幸徐賢妃,廢掉太子,改立徐賢妃所生的兒子王宗衍。宗衍登基後把宗字去掉改名王衍,是為前蜀後主。後主登基後,尊母親徐氏為皇太后,又尊姨母徐淑妃為皇太妃。這姐妹倆貪狠非常,發明了官員崗位拍賣制,從刺史以下,每缺一官,就暗行拍賣,誰給的錢多誰就上位。就此猶嫌不足,另派親信在通都大邑建起官營的旅店商舖,跟老百姓爭利。
王衍繼承了母系的惡劣基因,非常荒淫無道。年少的時候就只管自己享樂,國事全部交給幾個太監,找了一些親近的小人,叫作狎客,大家一起耍。王衍建造了很多漂亮的宮捨,跟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有一年的重九,他又大擺宴席,嘉王王宗壽流淚進言,說皇帝你一定要注意啊,這樣下去國家就要危殆了。那些狎客何嘗把王爺放在眼裡,就說嘉王是喝醉了不由自主地流淚,叫作「 酒悲」,然後一起去辱謾嘲笑他,王衍卻在一旁作壁上觀,漠然視之。
王衍還有一個愛好是微服出遊。當時蜀人性好新奇,流行一種特別小的帽子,只能蓋住頭頂,一低頭帽子就掉下來,號稱「 危腦帽」,王衍認為危字不祥,於是頒令禁戴。他別出心裁,喜歡戴大帽,後來人們只要一見戴大帽的就知道是他,他又令都城中人必須都戴大帽。王衍還發明了一種新式玩意兒,就是把頭巾裹在頭上,裹得尖尖的像個錐子,這或許就是土改、「 文革」 時給「 土豪劣紳」 「 地富反壞右」戴的高帽子的濫觴。後宮的女子,也都戴上金蓮花冠,就是用金箔折成蓮花狀的帽子,再穿上道士服,把臉頰塗紅,號曰「醉妝」。太后太妃游青城山,隨行宮娥衣服上都畫著雲霞,飄然若仙。其好逸荒政,往往若是。
王衍要是生活在現代社會,可以做一名優秀的時裝設計師,或是會所設計師,命運卻使他做了一名帝王。這是老百姓的大不幸,然而他自己又何嘗幸運?其下場很是悲慘,國家亡給了後唐莊宗李存勖,全家上下也均被殺害。莊宗本來應承,只要王衍歸降,不失封侯之位,但因伶人進讒,莊宗還是背信棄義,殺了王衍一家。殺到徐太妃時,徐太妃說:我兒子帶同一國誠心歸降,你卻如此無信,將來必遭報應。後莊宗果為伶人所弒。
王衍有一首《醉妝詞》流行於世:
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盃酒。
詞中的「 者」,今天寫作「 這」。這首詞篇制十分短小,卻有一種豪宕不羈之氣。我在北大讀書時的老師張鳴先生,非常不喜歡這首詞,但是我的至友陸傑,卻覺得此詞非常有帝王氣象。陸傑可以找到他的知音,那就是古龍先生。古龍先生在《大旗英雄傳》第二十一章《武道禪蹤》裡邊,寫到夜帝之子朱藻出場時,便是以手拍腿,高歌此詞。古龍評價說:「這闕《醉妝詞》,乃是五代殘唐蜀主王衍所寫,此刻在他口中歌來,果然有一種帝王之豪氣。」
我也覺得這是一首好詞,它展示的是拋開世間俗務,追求純粹的快樂的生命精神。其實,如果一名帝王只是耽酒好色,並不是多壞的事情,最壞的是喜歡折騰,折騰老百姓,今天一個想法,明天一個主義,老百姓就沒有好日子過了。孔子說過:「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統治老百姓其實很簡單,就是像北斗星一樣端居天中,清靜無為,不去多打擾老百姓的正常生活,與民休息,自然天下大治。這是題外話,表過不談。
總結一下,前蜀是一個人情澆薄、習於奢侈的國度,它的君主後主王衍又是一個荒淫無道、不理政事的昏君。問題來了,這樣的國、這樣的君,值得德潤為之守節不移,甘當遺民嗎?
我們看一看陳寅恪先生《王觀堂先生輓詞序》就明白了。
王觀堂,即學術大師王國維。他曾任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導師,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四大導師。他本是前清秀才,後在上海東文學社得名學者羅振玉的賞識,由羅資助東渡日本留學。王國維在日本開始做甲骨文研究,暨宋元戲曲研究,後來終成大師。清朝雖亡,羅振玉卻仍忠於清室,他得到已經遜位的末代皇帝溥儀的賞識後,便挈帶王國維做了南書房行走的五品官。而到1927年,因先有軍閥馮玉祥部下鹿鍾麟,不顧國民政府與清室簽訂的《清室優待條約》,把溥儀和整個皇室趕出宮去,又有大學者葉德輝在湖南被槍斃,王國維深受刺激,選擇於1927的6月2日,夏歷端午的前二日,寫了一封遺書放在口袋裡,跟他的學生借了兩塊錢銀洋,租了輛黃包車直到頤和園,在魚藻軒邊投入昆明湖自盡。昆明湖水並不深,但王國維是頭下腳上,一頭栽進去的,湖底的淤泥把他的口鼻塞住了,不旋踵即窒息而亡。屍體被撈上岸時,衣服還沒有完全濕透,遺書的字跡也十分清晰,開頭四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王國維的自殺,對清華師生觸動殊巨。此事一發生,梁啟超就召集學生訓講,把王國維跟屈原並論。陳寅恪先生則寫了一首長慶體的詩《王觀堂先生輓詞》以表哀思,這首詩是學唐代元稹的《連昌宮詞》,前有小序,大旨是認為王國維之自沉,不是殉清,而是殉人倫、殉文化。裡邊最有名的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
所謂的「 三綱六紀」,「三綱」 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六紀」 指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以君臣之綱而言,就算皇帝是像李煜一樣無能的君主,也要把他當光武帝劉秀那樣的英主看待;以朋友之紀言之,就算朋友是酈寄,也要把他像鮑叔一樣對待。酈寄是初漢時人,與呂祿為友,呂後擅權時,把劉氏宗族幾乎殺光,大漢快變成呂家的天下了。酈寄欺騙呂祿,騙得兵符,交給太尉周勃,於是周勃等人就把諸呂全部誅殺。鮑叔是春秋時人,他跟管仲是好朋友,兩人合夥做生意,賺來的錢管仲給自己分得多,給鮑叔分得少,鮑叔不以管仲為貪,知他有老母在堂需要供養;管仲用鮑叔的本錢做生意,虧了好多錢,鮑叔不認為他愚笨,而歸咎於時運未濟。在陳寅恪先生看來,三綱六紀都不是外在的道德規範,而是內心的道德律令,是個人所應追求的道德上和文化上的理想。
所以,德潤給這樣的國守貞,給這樣的君主守節,這是他的精神理念超拔之處,正體現出他高岸的人格。說他不懂得權變,不懂得順應時代,這樣的思想恰恰是卑賤庸俗的小人之見。正因歷次改朝換代,都有不食新朝俸祿的大人君子在,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觀才能代代綿延。
德潤選擇這樣的人生道路,固然與他深受儒學熏染有關,但根本上是因為他生具堅強不磨的性情。也正因有此性情,他的詞才在婉麗中透出貞剛的力量。
浣溪沙
晚出閒庭看海棠。風流學得內家妝。小釵橫戴一枝芳。鏤玉梳斜雲鬢膩,縷金衣透雪肌香。暗思何事立殘陽。
訪舊傷離欲斷魂。無因重見玉樓人。六街微雨鏤香塵。早為不逢巫峽夢,那(nuo )堪虛度錦江春。遇花傾酒莫辭頻。
第一首寫一位女子,向晚時分,閒愁難遣,到庭院中看海棠消悶。她態度風流,學得了宮中的裝束,把一枝小釵橫插在髮髻上,這髮釵上,還沾有她的體澤,因此一定也是芬芳的。古典詩詞的美,妙處往往難言,有時需要讀者調動眼耳鼻舌身全部的感覺器官,才能深入體悟。像唐詩「 蜻蜓飛上玉搔頭」,其幽微隱約之旨,必得用嗅覺感知。「 小釵橫戴一枝芳」 也是這樣。這位女子的鬢髮髮質特別光膩,濃密得像雲一樣,那是用美玉雕鏤成的梳子梳就的,她穿著金縷衣,透出雪樣的肌膚,她的體香令人發狂。可是,這樣令人愛慕不已的女子,心中一定有什麼解不開的幽恨,她定是想起什麼來了,在殘陽下含情悄立,忘記了傍晚時分,夜露風寒。這首詞與《花間集》中很多作品風格相似,但「 暗思何事立殘陽」 一句,寫得非常峭直,非常有力量,這是用一句結句對前面五句的意思進行了翻轉,因此也就更耐人尋味。清代大詞人納蘭性德也有一首《浣溪沙》:
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思往事立殘陽。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
「沉思往事立殘陽」,實際上就是學的「 暗思何事立殘陽」 這一句。
第二首中「 早為不逢巫峽夢,那堪虛度錦江春」兩句,在當時非常流行。但是我認為大眾並沒有判別文學經典的能力,能夠流行的,往往並不是真正高妙的作品,或者雖然是高妙之作,大眾只是震炫於一些表層的東西,並不能真正理解作者的苦心孤詣。方殘唐五代之時,社會動盪,整個社會人情澆薄,普通人生活朝不保夕,成日想的就是醉生夢死,所以他們讀到「早為不逢巫峽夢,那堪虛度錦江春」 這兩句時,自然感到「於我心有慼慼焉」。但實際上,德潤要表達的並不是這種對自己的人生放任自流的意思。李冰若先生不愧是花間詞的知音。他指出:
無因重見玉樓人,故遇花沽酒莫辭頻。非曰及時行樂,實乃以酒澆愁,故其詞溫厚不儇薄。
這是情深之至的傷心人語,而不是儇薄無行之輩的情慾放縱。
《花間集》中有很多儇薄的詞,如張泌的《浣溪沙》:
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回嬌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計是,便須佯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
魯迅翻譯如下:
夜趕洋車路上飛。東風吹起印度綢衫子,露出腿兒肥。亂丟俏眼笑迷迷。難以扳談有什麼法子呢?只能帶著油腔滑調且釘梢。好像聽得罵到「 殺千刀」 !
德潤的《浣溪沙》氣息完全不同。他不是要表現人生苦短及時行樂,不是在描寫放縱,而是刻畫出一個為愛執著,不惜用酒麻醉自己的情種形象。
浣溪沙
紅藕花香到檻頻。可堪閒憶似花人。舊歡如夢絕音塵。翠疊畫屏山隱隱,冷鋪紋簟水潾潾 。斷魂何處一蟬新。
詞的上片,以紅藕花香頻吹入窗台起興,逗引出閒情悶悶,思念佳人,不堪相思之苦。「舊歡如夢絕音塵」,是說從前兩個人在一起的快樂日子現在就像做了一場春夢,朦朦朧朧無法捉摸,隔斷了音塵。一個「絕」字,用得非常見力度。過片描繪內室屏風寢具的精美,隱藏的意思卻是因相思而失眠,因為只有失眠的人,才會有心思關注屏風寢具。屏風上畫著重重疊疊的青山,綿綿不斷,就像是我對伊人的思念;清涼沁骨的細竹蓆上有美麗的花紋,鋪在床上,彷彿粼粼碧水。如此精室,可堪獨宿?唯有相思割不斷,吹不去。結句「 斷魂何處一蟬新」,蕭繼宗教授對其評價是:「情境交融,盡遺俗腐。」「盡遺俗腐」 的意思是不做尋常套語,而能寫出新的儀態來。「一蟬新」,是說驀地聽到秋蟬的鳴叫,才忽然意識到,哦,秋天到了,而我竟然整個夏天都是在思念、煎熬中度過。夏季蟬鳴不絕,但唯有秋蟬孤鳴之聲,才讓人「 斷魂」,才讓人感到蟬鳴之「 新」。這是一種移情於物的手段,隱藏的意思是,我的痛苦只有這孤獨的秋蟬能夠知會吧。
德潤的一些作品,可說是花間詞的別調:
漁歌子
楚山青,湘水淥。春風淡蕩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棹歌相續。信浮沉,無管束。釣回乘月歸灣曲。酒盈樽,雲滿屋。不見人間榮辱。
荻花秋,瀟湘夜。橘洲佳景如屏畫。碧煙中,明月下。小艇垂綸初罷。水為鄉,蓬作捨。魚羹稻飯常餐也。酒盈杯,書滿架。名利不將心掛。
柳垂絲,花滿樹。鶯啼楚岸春山暮。棹輕舟,出深浦。緩唱漁歌歸去。罷垂綸,還酌醑。孤村遙指雲遮處。下長汀,臨淺渡。驚起一行沙鷺。
九疑山,三湘水。蘆花時節秋風起。水雲間,山月裡。棹月穿雲遊戲。鼓清琴,傾淥蟻。扁舟自得逍遙志。任東西,無定止。不議人間醒醉。
德潤在蜀亡之後,可能到湖南一帶隱居。這組詞大概就是寫隱居高曠之情,詞中充盈著勃勃的生機。
第一首的「 酒盈樽,雲滿屋」 寫得最好。戰國時偉大的思想家莊子,提出一個重要的哲學概念,「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這兩句就表達了這樣的生命精神。
第二首相對上一首,微嫌刻意,但仍可見德潤胸次之開闊。「酒盈杯,書滿架」及不上「酒盈樽,雲滿屋」,何妨做一個不識字的漁夫呢?這才是更高曠的境界。德潤畢竟是儒生,他可以放下名利,放下小我私己,卻放不下士大夫與生俱來的東西:憂患意識。所以他還是忘不了他的「 書滿架」。
第三首起句「 柳垂絲,花滿樹。鶯啼楚岸春山暮」,實化自南朝丘遲《與陳伯之書》中的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整首寫出了作者與天地合一、宇宙交融的襟抱。「下長汀,臨淺渡」,好像看起來跌宕很大,實際上一丘一壑,盡在漁翁胸中。
第四首「 水雲間,山月裡。棹月穿雲遊戲」,寫得多好,一顆心隨著月亮,穿雲遊戲,月亮就彷彿是一條小船,一顆心就是這條小船上的撐篙人。宋儒常講,「鳶飛魚躍,活潑潑地」,這顆心正該如此。「鼓清琴,傾淥蟻。扁舟自得逍遙志。」淥蟻一般寫作綠蟻,是酒的別稱,新釀的酒,一般是乳白色,放上一段時間,顏色會變綠,上面浮著一層薄沫,乍看像螞蟻一樣,故稱綠蟻。鼓琴飲酒,扁舟自適,該是很多人嚮往的境遇吧!「 任東西,無定止。不議人間醒醉。」抒寫的是忘懷物我的自由境界。「 不議人間醒醉」用《楚辭·漁父》之典。屈原被放逐後,行吟澤畔,形容枯槁,遇一漁父,互相對答,屈原說自己落到如此田地,是因「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勸他不如和光同塵,從俗全己,屈原不從,決意投水自沉,漁父莞爾一笑,敲著船槳,唱著《滄浪歌》離去。這個故事是儒家人生觀與道家人生觀的一次交鋒,到德潤這裡,卻同時超越了屈原與漁父,他是「 不議」 人間醒醉,真正達到了莊子「 齊物」 之境。
巫山一段雲
古廟依青嶂,行宮枕碧流。水聲山色鎖妝樓。往事思(si )悠悠。雲雨朝還暮,煙花春復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
這首《巫山一段雲》,龍榆生先生《唐宋名家詞選》選過,是一首千古名作。《巫山一段雲》詞牌出自戰國時楚國辭賦家宋玉的《高唐賦》,是講楚頃襄王夜宿高唐,半夜有一女子與之歡會,自述:「妾乃巫山之神女,朝為行雲,暮為雨,朝朝暮暮,陽台之下(hǔ )。」德潤的這首《巫山一段雲》,也是詠巫山神女的本意之作。不過,此詞借古諷今,有強烈的現實感,因此也就別出機杼。上片借古廟行宮眼前之景起興,想像巫山神女正在水聲山色之中,轉以感慨興亡,由楚頃襄王的荒淫無道,映襯蜀後主王衍,故曰「往事思悠悠」。過片是說,巫山雲雨,依然朝朝暮暮,何嘗真見神女其人?像輕煙一樣縹緲美麗的花兒,年年盛開,可是當年地連千里的大國楚,今又何在?二句感慨非常。三峽兩岸的猿啼非常有名,《水經注》記載:「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 zhǔ) 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 猿啼本已備極哀戚,行客之哀,卻又更甚於猿啼了。「行客自多愁」 並不是游宦在外,漂泊思鄉之愁,而是亡國之人,眷懷故國之哀。
德潤的作品突破了花間詞專寫男女情愛的習慣,觸及更加廣闊的社會情形,尤其是用詞來描寫南國風土人情,以十首《南鄉子》,最臻其妙。茲舉三首:
煙漠漠,雨淒淒。岸花零落鷓鴣啼。遠客扁舟臨野渡。思鄉處。潮退水平春色暮。
漁市散,渡船稀。越南雲樹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聽猩猩啼瘴雨。
相見處,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裡回眸深屬意。遺雙翠。騎象背人先過水。
下面這兩首我認為是寄托亡國情懷的作品。一首《菩薩蠻》:
回塘風起波紋細。刺桐花裡門斜閉。殘日照平蕪。雙雙飛鷓鴣。征帆何處客。相見還相隔。不語
欲魂銷。望中煙水遙。
「 相見還相隔」,相隔的不是一個特定的人,而是他所思念、所緬懷的故國,所以才有「 不語欲魂銷。望中煙水遙」 之慨。煙水相隔,遠望不見,隱喻過去的所有美好、所有歡樂,再也追不回來了。這個國再壞也好,再怎麼樣也好,也是我的家園。「殘日照平蕪。雙雙飛鷓鴣」 二句,上句闊大,下句纖微,上句凝重,下句輕靈,藝術手法非常高明。
《西溪子》同樣應該是有寄托的作品:
金縷翠鈿浮動。妝罷小窗圓夢。日高時,春已老。人來到。滿地落花慵掃。無語倚屏風。泣殘紅。
此詞表面上是講女子思春,慵懶無聊,偶因所觸,流過臉頰的眼淚和著胭脂,就成了「 紅淚」。實際上,更像是一位遺民,對著已亡之國灑下的哀涼之淚。「泣殘紅」 暗用三國時薛靈芸紅冰之典,她被征送入宮,臨行哭泣不已,以玉唾壺承淚,壺呈紅色。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冰。故後世以「 紅冰」 「 紅淚」 代指女子的眼淚。
德潤還有未選入《花間集》的一些作品,也很有特色,如《漁父》三首:
水接衡門十里餘。信船歸去臥看書。輕爵祿,慕玄虛。莫道漁人只為漁。
避世垂綸不記年。官高爭得似君閒。傾白酒,對青山。笑指柴門待月還。
棹警鷗飛水濺袍。柳侵潭面柳垂絛。終日醉,絕塵勞。曾見錢塘八月濤。
曠達中見深婉。還有一首《定風波》:
往事豈堪容易想。怊悵。故人迢遞在瀟湘。縱有回文重迭意。誰寄。解鬟臨鏡泣殘妝。
清末大詞人況周頤認為有「 故君故國之思」,我認為這種說法是成立的。況周頤認為:「李秀才詞清疏之筆,下開北宋人體格。」強調他風格的獨特。李冰若則說:「 李德潤詞大抵清婉近端己,其寫南越風物,尤極真切可愛。在花間詞人中自當比肩和凝而深秀處且似過之。……花間詞人能如李氏多面抒寫者,甚鮮。故余謂德潤詞在花間可成一派而可介立溫韋之間也。」則是將德潤與溫、韋並列為三大家了。我以為,德潤詞的妙處在於包羅萬象,他不是把詞只當成應酬歌女的工具,而是用它來抒情、憂患、白描、交往,這實際上是把詞當作詩來寫,拓展了詞的功能。
與德潤同時有個叫尹鶚的人,寫詩嘲諷他:「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熏來也不香。」出語輕薄,徒令人不齒。其實五代十國士大夫風骨掃地,能夠有一個波斯人,接受儒家文化熏陶,堅強不磨,是該讓當時很多士大夫羞愧的。故清代周之琦評價德潤,最稱公允:「雜傳紛紛定幾人。秀才高節抗峨岷。扣舷自唱南鄉子,翻是波斯有逸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