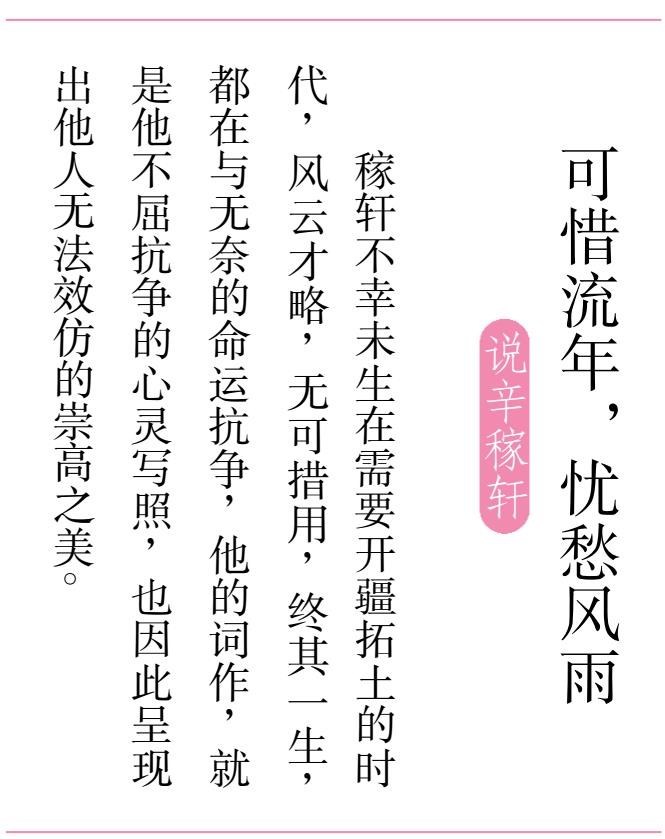

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四月,北方女真族政權金國攻破宋都汴梁,擄劫徽、欽二帝北上,同時被擄的還有皇族後宮、大臣名公、樂工巧匠、平民百姓不下十萬人,太平百年宋都所積累的財富,也被金人洗掠一空。宋徽宗於被擄路上,作有一闋《燕山亭·北行見杏花》,詞中感慨:「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發語淒斷,令人腸斷氣結。金人剝奪了他的一切,甚至包括最後的尊嚴,亡國之君,欲求一死而不可得,使人思之惻然。
金人擄走徽、欽二帝后,立太宰張邦昌為帝,成立偽政權,國號大楚。張邦昌只做了三十二天偽皇帝,即擁戴康王趙構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 登極,年號建炎。康王曾在金國為人質,對金人懼若豺虎,遂決意南逃建康(今江蘇南京),主戰的李綱、宗澤均被他削權投閒。他先以揚州為行在(天子巡行駐蹕的地方) ,又一路南逃,升杭州為臨安府,意為臨時安頓,其實是想長安於此。金人一路追擊,康王直逃到海上,漂泊三十餘日,始得脫險。戰爭延至宋高宗紹興十一年(1141),宋金雙方簽訂和議:宋向金稱臣,由金國策封趙構為皇帝,大散關至淮水以北,土地人民不再為宋所有,宋國每年向金國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從此開啟了一百餘年偏安苟且的南宋。
在連年的戰爭中,無論士大夫還是普通老百姓,莫不顛沛流離,受盡苦楚。這是一段血淚交迸的歷史,而在這期間湧現出的不少詞作,都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意識、愛國情懷,感激時事、慷慨悲歌之作,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其中健者,則有朱敦儒、陳與義、葉夢得、張元幹 、向子諸人。
如朱敦儒《水龍吟》詞感慨「 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惋惜自己「 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只得「 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淚流如雨」 ;他眼中的這段歷史,「個是一場春夢,長江不住東流」(《臨江仙》),他向蒼天發問「 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最終卻是「 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 (《相見歡》),歸於一場慟哭。葉夢得不忿於「 邊馬怨胡笳」,胡人侵佔中原,祈盼有一位像謝安一樣的英明統帥,「談笑淨胡沙」 (《水調歌頭·秋色漸將晚》) 。張元幹 贈胡邦衡、李綱的二首《賀新郎》,更是激越蒼涼,氣沖牛斗。
然而,這一類被文學史家稱為「 豪放詞」 的作品,情感過於直露,詞中的意象,都是為了烘托情感而生生拉扯過來的「 造境」,令人一覽無餘,沒有可供細品的餘味,稱不上第一流的詞品。更重要的是,這類作品產生於戰亂連綿、國破家亡的時代,時代裹脅了每一個人,於是便出現了這些沒有個性、只有共性的詞作。在乾坤板蕩的時局下,個人的自由心靈變得不再重要,詞人的哀怨憤激,都不得不附麗於時代,詞作難以產生超越時代的藝術價值。而我們知道,真正偉大的作品,一定是超越時代的。
直到辛稼軒橫空出世,南宋詞壇才有了全新的面目。
稼軒名棄疾,字幼安,出生於山東歷城,他出生時,北方已淪陷於異族十三年了。稼軒的祖父辛贊,雖然在金人的統治下做著小官,卻心懷大宋,「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 (辛棄疾《進美芹十論札子》) 。稼軒從他的祖父那裡接受了儒家正統思想,他不僅以士大夫名節自勖,更以恢復中原、致君堯舜作為其畢生信仰。稼軒不僅有英雄情懷,更有英雄手段,他的詞是英雄之詞,與一般文人的詞作殊觀。
歷來說詞者多把蘇、辛並舉,謂為「 豪放派」 的代表人物,且每以為辛詞學自蘇詞;只有清代周濟《宋四家詞選》,以稼軒「 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為「 領袖一代」 之大家,反以蘇詞附於辛詞之下,崇辛抑蘇,堪稱獨具只眼。周濟又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比較蘇、辛,曰:「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情富艷,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世以蘇、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之;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語也。」拈出「 才情富艷,思力果銳」 八字,的是知音,又說「 稼軒固是才人,然情至處,後人萬不能及」,更是深有味於斯道的卓見。唯稼軒之高卓,不僅在於其沉鬱悲涼、耐於尋繹的詞味,更在於他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具有古希臘悲劇英雄氣質的詞人,他的詞中,跳躍著的是與古希臘悲劇一樣的崇高精神。
悲劇(tragedy )一詞,起源於古希臘,本意是「 山羊之歌」。古希臘人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以歌隊侑神,所有歌隊中人都穿著山羊皮,戴著羊角,裝扮成酒神侍從薩提爾的樣子,歌頌酒神,後來慢慢發展為代言體的戲劇形式。古希臘悲劇多演神的故事,所謂的悲,不是悲傷之悲,而是悲憤激越之悲,悲劇中激盪著的是強大的生命意志。
悲劇的美學旨趣是崇高。一切悲劇,最終都要帶給人以崇高感。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魯迅對於悲劇的定義。他說,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是將那些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魯迅的這種看法,其實也不是他的發明。西哲亞里士多德就認為,悲劇要描寫比我們高尚、比我們要好的人,而喜劇則是要描寫比我們卑賤、比我們要差的那些人。這一說法,並沒有把握住悲劇的本質。
我個人最欣賞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對悲劇的定義。黑格爾說:「在悲劇裡,個人通過自己的真誠願望和性格的片面性來毀滅自己。」悲劇主人公性格的片面性與他的真誠願望產生衝突之時,他沒有選擇放棄、逃避、妥協,而是選擇了猛銳抗爭,殞身不恤,最終,主人公毀滅了自己,卻張揚了他的生命意志,在毀滅之火中放出絢爛的光芒。
西方傳統上把悲劇區劃為命運悲劇與性格悲劇,如古希臘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是命運悲劇,而莎士比亞的名劇《奧賽羅》則是典型的性格悲劇。但天命之謂性,天之所賦,不可改,不可易,性格也是一種命運。面對天命,人不再只是順從,而是以其強有力的生命意志,勇於抗拒天命,不畏犧牲,展露出人性的高貴莊嚴,這正是悲劇精神的價值所在。稼軒就正是這樣一位悲劇英雄。
古希臘悲劇主人公起先都是神,後來也開始表現有神的血統的英雄人物,他們通常都是勇武過人、才智出眾之士。稼軒武藝超群,膽略過人,一生力圖恢復中原故地,卻不能一騁其志,反而累遭投閒置散。他的人生荒廢了將近二十年,原因在於,當時南宋的基本國策是向金國屈膝求容,而非掃平胡氛。「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 (劉克莊《沁園春·夢孚若》) ,稼軒不幸未生在需要開疆拓土的時代,風雲才略,無可措用,終其一生,都在與無奈的命運抗爭,他的詞作,就是他不屈抗爭的心靈寫照,也因此呈現出他人無法效仿的崇高之美。
當然,稼軒與西方悲劇主人公不一樣的是,他沒有像西方的悲劇主人公那樣,最終走向毀滅。但實際上,他通過燃燒自己的生命,讓生命的餘燼化成傳之不朽的詞作,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生命毀滅。也正因此,他的詞作才尤其動人。
我們對比蘇詞與辛詞,會對稼軒詞中的悲劇意識有更深切的感受。他們之間的分別,不是前人所謂的蘇才高而辛力大,實以蘇之生命精神偏於沖淡,不若辛之生命,如大火烈焰,有悲劇感,有崇高感而已。譬如同是讀老、莊,蘇、辛二家,亦絕不雷同。東坡是儒釋道三教俱完足於心,讀莊子,尤深洽於心;稼軒卻一生恪守儒學,對道禪雖未明斥,內心終是格格不入。而儒學本就是偏於悲劇情懷的一門學說,孔子被石門晨門稱作「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曰捨生取義,都是偉大的悲劇精神。歷代儒生,每多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士,他們能在乾坤板蕩之際做出猛銳的選擇,其實都是從孔子那裡繼承了悲劇的性格基因。
感皇恩·讀莊子聞朱晦庵即世
案上數編書,非莊即老。會說忘言始知道。萬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霽,青天好。一壑一丘,輕衫短帽。白髮多時故人少。子雲何在,應有玄經遺草。江河流日夜,何時了。
朱晦庵是南宋理學家朱熹。當時他的學問已被朝廷宣佈為偽學,嚴禁士子傳習,朱熹既歿,門生故舊都不敢去送葬,稼軒卻不計個人安危,寫了這首詞以為弔唁。選擇《感皇恩》這個詞牌,其實是對皇帝的諷刺。表面看,這首詞用到了一些老莊的哲學思想,顯得頗有曠達之思,但是詞人又說,老莊之學,是要人忘言、忘情,自己卻是「 不自能忘」,他眷情於故人多已下世(白髮多時故人少) ,他心中的怨苦,便如江河日夜奔流,無有已時。由此可見,稼軒與老莊之學,本質上是格格不入的。
人們往往把蘇、辛並稱為豪放詞人,其實《東坡樂府》中豪放之作滿打滿算也超不過十首,辛詞固不乏粗豪之作,但是與豪放的精神——豪情高縱、滿不在乎——並不特別契合。無論對哪一位詞人來說,粗豪都不是一個優點,而是一種毛病,只是稼軒才大,使人不覺粗豪為病耳。比如京劇中的麒派,是啞著嗓子唱戲,固然有其濃墨重筆的潑畫之美,但啞嗓子終究是毛病,不如高亮窄的老生嗓子受聽。如《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只好算是一篇合韻的史論,卻離詞心、詞味相距遼遠。
又如《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
名。可憐白髮生。
雖然虎虎生氣,終嫌一瀉無餘,缺乏詞味。只是他情感熾熱,真力瀰漫,方能救粗豪之失,不墮於叫嘯一路。
與其說辛詞的風格是豪放的,倒不如說辛詞是包羅萬象的。在稼軒那兒,無一事不可入諸詞,生活中猥瑣平庸的小事,他都可以寫入詞裡面,且別饒天趣。他又豈但是以詩為詞而已,文、賦各體,莫不可入諸詞。在他投閒置散將近二十年的漫長歲月裡,他更是把詞當成排憂遣悶的遊戲,以近似於俄羅斯學者巴赫金所謂的「 狂歡化」精神去寫作。如下面這一首《水龍吟》:
聽兮清珮 瓊瑤些。明兮鏡秋毫些。君無去此,流昏漲膩,生蓬蒿些。虎豹甘人,渴而飲汝,寧猿猱些。大而流江海,覆舟如芥,君無助、狂濤些。路險兮、山高些。愧余獨處無聊些。冬槽春盎,歸來為我,制松醪些。其外芳芬,團龍片鳳,煮雲膏些。古人兮既往,嗟余之樂,樂簞瓢些。
此詞是稼軒第二次被貶,在江西瓢泉蟄居八年之時所寫。詞前有小序,曰:「用些(suo )語再題瓢泉,歌以飲(yin )客,聲韻甚諧,客為之酹。」所謂「 些語」,就是每一句的句末,都用「些」字作為語助詞。「些」字是楚方言,楚辭的名篇《招魂》中,就以此字作為句末語助詞。這首詞的真正的韻腳,是「 些」字前面的那些字:
瑤、毫、蒿、猱、濤……這樣的詞,既不是言志之作,也非緣情而發,它只是在表達一種諧趣,大約從俳諧文發展而來,是十足十的遊戲筆墨。
復如《沁園春·將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喜睡,氣似奔雷。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此,歎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為媒。算合作平居鴆毒猜。況怨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為災。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則須來。
這首詞把酒杯給擬人化了,詞人絮絮叨叨,列數對酒杯的不滿,疏狂之態可掬,詼諧之致可喜。雖然它絕非文學,缺乏文學應有的感人的力量,但也算拓宇開疆,為詞之一體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稼軒寫這類詞是因為他滿腔的精力無法宣洩,無聊到極點,只好把文字當作遊戲。
幸好稼軒不是只有這樣的作品。辛詞之佳妙,不在其「 橫放傑出」 (晁無咎評蘇軾詞之語) ,粗豪跌宕,不在其「 橫豎爛漫」 (劉辰翁《辛稼軒詞序》) ,無一事不可入詞,而在其常能婉麗嫵媚,卻又風骨凜然。他集中佳作,總是那樣冷艷而淒厲,如子歸啼血,嫠婦夜起,在沉鬱的況味中蘊藏著悲劇性的崇高。
青玉案·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元夕即元宵,農曆的正月十五,是中國古代城市不行宵禁,男女自由約會的日子。這首詞上片先以「 東風」 三句,寫出元宵燈市迷離惝恍之美,再承以「 寶馬雕車香滿路」,極寫人流繁密。「鳳簫聲動」 是說春色漸近,古人詩句中,凡涉「 鳳簫」 一詞,多在春日;「 玉壺」則是用以滴水計時的滴漏壺,「玉壺光轉」,是說時光在玉壺滴瀝的水聲中悄悄流逝。一夜之中,各種形制的花燈紛紛披呈,彷彿魚龍戲舞,千奇百怪。上片的風格,是十分峭直的。
過片承「 元夕」 之題,寫詞人遇見一位絕色佳人,她的頭上插著美麗的頭飾,笑語盈盈,從身邊走過,空氣中還留著她身體的幽香。詞人很想與之交言,卻到處覓不著她的蹤影,不期然地回首一瞥,卻見到她正在燈火零落將盡的所在,悄然站立。「眾裡尋他千百度」 的「 度」,是宋時方言,今天廣東話依然保留,意即「 處所」。相對於上片的峭直,下片風格轉為婉麗深沉。
這是一首有寄托的作品。稼軒把自己與這位佳人的關係,比喻為與皇帝的君臣遇合。他渴望獲得朝廷的信任,好讓他披甲沙場,恢復中原。然而,心中的「 她」卻終是可望而不可即。但在讀者讀來,並不覺淒婉,便因詞人有著「 眾裡尋他千百度」 的執著情懷,這是與命運抗爭的悲劇精神,詞的風骨也正因此而得以呈現。
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
這是一首借登山臨水而弔古傷今的名作。郁孤台建在贛州以北賀蘭山頂,以山勢高阜、郁然孤峙而得名。據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三:「吉州吉水縣,江濱有石材廟。隆佑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 速行,虜至矣!』 太后驚寤,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稼軒即因此史實而生感慨。
詞的上片,先寫往來登臨郁孤台之人,心懷忠憤,感慨當日金人險些追及隆佑太后的奇恥大辱,不由得淚水濺入清碧的江水之中。江水奔流不盡,而行人的傷心之淚,也橫流無盡。登台向西北望去,哪裡能見到故都汴梁?只見重重疊疊的山,遮住了望眼。隱喻故都已淪於金人之手。過片承上「可憐無數山」 頂針寫下去,「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二句,表面上是講贛江之水不為青山所阻,滔滔不息,奔流到海,實際上是說神州貴胄,雖遭一時折辱,終當重新奮起。然而,朝廷終無恢復中原之志,詞人心中本已積鬱難開,更何況聽到深山中鷓鴣的哀叫?無限哀涼心事,自然盡在不言中了。鷓鴣似山雞而體型較小,其叫聲像是在說「行不得也哥哥」。山中何鳥不鳴?詞人偏說聽著鷓鴣啼,是說恢復之事行不得,意蘊極為深長。
清平樂·獨宿博山王氏庵
繞床饑鼠。蝙蝠翻燈舞。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發蒼顏。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
此詞音節繁密,急如擂鼓,沉鬱之至,而又崇高之至。詞人行經博山(治屬今山東淄博) 一帶,在一戶王姓人家投宿;庵,圓形的草屋。詞的上片,描寫宿所的簡敝:老鼠覓不著食物,夜中繞著床鋪活動;門窗殘破,蝙蝠飛入屋中,圍著燈火翻飛;大風吹著屋頂上的松樹,松葉搖得沙沙響,彷彿是一陣驟雨;糊在窗欞上的窗紙,也已殘破不堪,發出低喃的聲響,如同有人在絮絮自語。在這樣的環境下,詞人的心境是沉鬱的、哀涼的,他自然地點檢平生心事,想起自己一生志在恢復中原,少年時受祖父所命,入燕京應舉,以刺探敵人虛實,後來南渡投宋,終不能一騁其志,年華虛度,只落得頭髮花白,容顏蒼老。但結二句陡然振起,謂秋夜夢迴,仍時時以天下江山為念。這種造次顛沛,不離於仁的悲劇情懷,與詞人的生命相始終,展現出崇高之壯美,也是稼軒詞最能動搖人心的地方。
稼軒是在淪陷區起義投奔大宋的。宋高宗紹興辛巳(1161),金主完顏亮讀了柳永的《望海潮》詞,欣然有慕於江南之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興立馬吳山之志。他舉大軍南侵,卻在採石磯被宋軍擊敗。其時完顏雍又在後方政變,登基為帝,侵宋的金人軍心不穩,遂發起兵變,殺死了完顏亮。金國內亂讓稼軒看到了恢復故土的希望,他結合了二千兵馬,舉義旗起義,投奔當時有二萬兵馬、號稱天下節度使的耿京,並被封為掌書記。稼軒還說服了另一支義軍的首領義端和尚歸順耿京。孰料義端首鼠兩端,一天晚上,偷走了耿京的軍印逃走,準備投降金人。耿京發現此事大怒,要以軍法處置稼軒,稼軒卻並不慌張,向耿京要求給他三天時間,必將義端拿獲,如事不遂,再來就死未晚,稼軒遂一路向金營追將過去,終於在半途追獲了義端和尚。義端自知性命不保,忙對稼軒說:「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義端大概善相術,他想挾此秘術乞得不死,稼軒當然沒有理他,逕斬其首,歸報耿京。這一年他才二十二歲。
稼軒被後人稱作「 辛青兕」,就是因義端說破他的「 真相」 這件事。他的好友陳亮這樣形容他的相貌:「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所謂背胛有負,就是說他肩部肌肉發達。稼軒的身材一定非常魁梧壯碩,他更像一位赳赳武夫,而不是文人。他讓我想起了清末台灣詩人丘逢甲。逢甲於清廷決定割讓台灣後,舉黑虎義旗抗日,號「 台灣民主國」,尊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自任副總統兼大元帥,抗日失敗後逃回內地,住在梅州蕉嶺。其《嶺雲海日樓詩鈔》力大無倫,其人外形也勇武非常,曾被人誤會是武進士。實際上丘逢甲自幼文采出眾,有神童之譽,是正途進士出身。這樣兼資文武的人才,在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他們更像是古希臘的悲劇英雄。
鷓鴣天
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 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 銀胡,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此詞記稼軒二十三歲時事。這一年,稼軒勸耿京奉表歸宋,既得首肯,遂與另一起義領袖賈瑞同去行在建康詣聖,帶回了南宋朝廷的任命書。其時耿京竟為叛將張安國所殺,獻於金人。辛棄疾親將五十騎,夜襲金營,活捉張安國,馬不停蹄,晝夜不食,終於押解著叛徒趕到新的行在臨安,交給朝廷,斬首於市。
稼軒的韜略智謀勇武,無一非上上之選,實在可以說是有改天換地之能,可是他終於不能一騁其志,這樣,他心頭的抑鬱憤激也就尤其過人。
稼軒歸宋以後,一心為天下蒼生計,以恢復中原為念,但朝廷只給他通判建康府、司農簿、知滁州、江東安撫司參議官、倉部郎官等內外官職,到前線與金人作戰,遙遙無期。這中間,他給宋孝宗上過《美芹十論》,分析敵我情況,提出中肯建議,又曾給丞相虞允文上《九議》,更具體地談恢復大計,這些主張,都是十分切實可行的,也體現出稼軒對兵事的深刻理解。怎奈有志恢復的宋孝宗和虞允文儘管很重視稼軒,宋孝宗還曾親自召見他,卻終因各方面的阻力,未能把他的主張付諸實踐。後來劉克莊、周密這些人都感慨,倘使稼軒的主張能為朝廷所用,歷史也許就會改寫了。劉克莊、周密的感慨不是無的放矢。稼軒既有卓絕的軍事天分,同時又是從淪陷區過來,深稔敵情,他的主張都是切實可行的。
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鱠 ,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捨,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 英雄淚。
這首詞是稼軒通判建康府時所作。歸宋已經有一些年頭了,英雄卻無用武之地,登高騁目,無非傷懷,清秋景致,益增哀涼。「楚天」二句,如畫潑墨山水,只用淡素的色澤,即刻畫出江南的凜然秋意。「遙岑」 三句,說的是眼中遠處的丘陵,彷彿是歌伎插著玉簪、盤著梳起的髮髻,她們唱著無聲的歌曲,傳遞著幽愁暗恨。「落日」 三句,以夕陽西下、孤雁唳叫的淒婉,映襯詞人客居江南,不得見用的淒涼心緒。自「 把吳鉤看了」 以下,情緒由淒婉頓轉激越。吳鉤是古代一種彎刀,唐代詩人李賀有詩云:「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稼軒即暗用此典。意謂,我一心要率兵北伐,收復失地,卻無法得到朝廷的支持,只能拍遍欄杆,縱情高唱,以一洩胸中塊壘,我的心事,又有誰真的懂得呢?過片情感又是一轉。詞人投宋後,不能效命沙場,只是做著地方官,不免偶興歸老之志,但他馬上自我否定了這種想法。晉代張翰字季鷹,當西風起時,想到家鄉松江的鱸魚蓴羹,於是掛冠歸隱。稼軒此處反用典故,意思是,不要說家鄉的鱸魚有多美味,西風起時,有幾人能如張翰一樣決然歸隱呢?方當天下擾攘之際,倘使像陳登一樣買地買房,我該被劉備那樣的英雄所恥笑吧!然而,壯志難酬,年華虛度,人生如在風雨之中,憂愁逼人。晉代大司馬桓溫,經過金城,看到從前自己做琅琊內史時所種的柳樹已有十圍( 兩手合拱 ) 之粗,感慨「 木猶如此,人何以堪」。稼軒也是深慨於歲月如流、人情易老,才問道:到哪裡去找貼心知己的佳人,為我揩拭英雄之淚呢?紅巾翠袖陰柔優美的意象,與英雄悲淚的壯美,形成了很高明的藝術張力,這就是沉鬱之境。
稼軒歸宋後第一次施展軍事才能,是在江西提點刑獄任上「節制諸軍,討捕茶寇」。茶寇是武裝暴動的茶商武裝。雖能統兵打仗,卻不是去打金人,稼軒心中,鬱積著不平,前引《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即作於這一時期。
平定茶寇後,辛由江西提點刑獄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今南昌) ,兼江西安撫,召為大理少卿,出為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轉運副使,仕途一帆風順。但稼軒要的是開赴前線,與金人交戰,他心中的怨懟也就越來越深。在由湖北轉官湖南時,他寫下了下面這首不朽名篇:
摸魚兒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恨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慇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樓,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詞借傷春著筆,而實蘊政治寄托。他用美好的春光比喻宋孝宗上台後一段短暫的力謀恢復、勵精圖治的政治景象。「畫簷蛛網」,喻指主和的朝臣。過片由「 長門事」 直至「 脈脈此情誰訴」,都是用漢武帝的皇后陳阿嬌的故事。傳說陳阿嬌失寵後,以千金請得司馬相如寫成了《長門賦》,冀以重返君心。詞人以陳阿嬌自況,「準擬佳期又誤」,是說皇帝本來是要支持恢復事業的,最終卻又變卦了。「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 是劈空而來的議論。君,指的是席間唱詞的歌伎。這三句的意思是,你這位在筵前歌舞的佳人,難道沒有看見,即使是楊玉環、趙飛燕那樣的傾國之色,也被人視為塵土?詞人這話似是對歌伎言,實際是在感慨自己,徒有千里之才,卻不得一騁其用。結尾的斜陽,卻是喻指皇帝,意謂:不要到高樓上徙倚,皇帝正在那煙柳銷魂蕩魄的地方宴安享樂呢!
此詞梁啟超評為「 迴腸蕩氣,至於此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諒非虛誇之詞。稼軒婉麗的辭藻背後,是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真氣,這正是稼軒詞悲劇精神的體現。
據羅大經《鶴林玉露》所載,宋孝宗讀到了稼軒的這首詞,也讀懂了「 斜陽煙柳」 背後的怨望,卻終於沒有降罪於他。這以後,稼軒又從湖南轉運副使改知潭州(長沙),兼湖南安撫使。到湖南後,稼軒得到朝廷許可,即發展地方武裝「飛虎軍」,費度巨萬。他的作風雷厲風行,事皆力辦,有人跟皇帝進言,說辛聚斂,發御前金字牌召他還京,稼軒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金字牌藏起,等飛虎軍建成,才把事情原委上復皇帝。此事雖未被孝宗怪罪,但還是引起朝廷的猜忌,不久就調他為兩浙西路提點刑獄。
稼軒不但做事雷厲風行,還敢於殺人,在湖北治盜賊,得賊即殺,不復窮究,一時奸盜盡皆屏跡。他的這種殺伐專斷的作風,不為當時的士大夫所容,所以很快被監察御史王藺彈劾,罪狀是「用錢為泥沙,殺人如草芥」。因為這個緣故,他在上饒帶湖所築「 稼軒」 投閒了十年,不被徵用。
光宗紹熙三年(1192),稼軒被重新起復,任福建提點刑獄,次年改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不到兩年,又被諫官劾為「 殘酷貪饕,奸贓狼藉」,從上饒遷往鉛( yan ) 山,再一次失意。這一回,他度過了痛苦無聊的八年時光。前後十八年,恰恰是一個人最能建功立業的壯盛歲月,卻被迫虛擲,稼軒內心的憤忿激越,不難想見。正因此,他的詞才尤其顯得真力瀰漫、元氣包舉。
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
綠樹聽鵜鴂 。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這首詞仿照的是南朝江淹《別賦》的寫法,羅列了一堆古人離別之事。上片寫昭君出塞、漢武帝皇后陳阿嬌失寵辭別漢闕而幽閉長門宮、春秋時衛國夫人莊姜辭別戴媯並賦《燕燕》詩,是怨別;下片寫蘇武別李陵、燕太子等人送別荊軻秦舞陽,是壯別。上片的怨別,用以烘托下片的壯別,更見壯別的悲壯崇高。如此羅列獺祭,卻不使人覺得雜亂無章,便因詞中激盪著充沛的悲劇精神,遂能大氣包舉,到海無盡。
漢宮春·立春日
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裊裊春幡。無端風雨,未肯收盡余寒。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卻笑東風從此,便薰梅染柳,更沒些閒。閒時又來鏡裡,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生怕見、花開花落,朝來塞雁先還。
上片「 春已歸來」 三句,是諷刺和議既成,一幫小人以為天下太平,從此無事,一個個打扮得妖妖嬈嬈,在頭上插上彩紙製成的春幡。(唐宋時人們會在立春之日,用彩色的紙或金箔製成小旗子,插在頭上,謂之春幡。) 可是敵人豈會就此甘休?「 無端風雨,未肯收盡余寒」。去年(年時) 的燕子尚未歸來,今夜應該夢到西園吧?在古詩中,西園多指皇家園林,這裡是說,連燕子都在懷念故都的園林,朝廷上下卻儘是一幫無心肝之輩。「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 三句,是說和議定得倉促,很多事務朝廷來不及處置。青韭堆盤,是立春時的風俗,把蔥韭等五種辛辣的蔬菜,生切了放在一盤中進食,用以發五臟之氣。
下片講這個小朝廷卻從此忘記了國仇家恨,開始粉飾太平。可是這種太平,是以忘記君父之辱、遺民血淚為代價的,它讓主戰派心中充滿難以言表的痛苦。我們的生命在閒中流逝,容顏也漸漸變得蒼老。我們心中的愁怨,便如九連環一樣,少有人懂得開解,更怕見春來春去,花開花落,一年年過去,從北方塞外之地飛來的大雁,捎帶來被囚在五國城的宋徽宗、宋欽宗的遺恨。周濟曰:「『 春幡』 九字,情景已極不堪。燕子猶記年時好夢,『 黃柑』 『 青韭』 ,極寫燕安鴆毒。換頭又提動黨禍;結用『 雁』 與『 燕』 激射,卻捎帶五國城舊恨。辛詞之怨,未有甚於此者。」古人作詩,講究「 怨而不怒」,稼軒此詞,卻是怨而且怒,他的心中積壓了太多的不平,憤然而鳴,當然不同凡響。
祝英台近·晚春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倩誰喚、流鶯聲 住。鬢邊覷。試把花卜心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嗚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將愁歸去。
朱庸齋先生《分春館詞話》云:「《祝英台近》句語長短錯落,必須直行之以氣,並用重筆,貫注迴盪,始稱佳構。試讀前人名作,莫不如此。如氣勢稍弱,則易破碎。稼軒『 寶釵分』 一詞,六百年間,無人嗣響,至彊 村『 掩峰屏』 始堪抗手也。」彊 村即清末詞人朱祖謀,他的《祝英台近》題作「 欽州天涯亭梅」,詞曰:「掩峰屏,喧石瀨,沙外晚陽斂。出意疏香,還斗歲華艷。暄禽啼破清愁,東風不到,早無數、繁枝吹淡。已淒感。和酒飄上征衣,莓鬟淚千點。老去難攀,黃昏瘴雲黯。故山不是無春,荒波哀角,卻來憑、天涯闌檻。」彊 村忠於清室,睹清之亡,以孤臣孽子之心,寫成此詞,方能與稼軒並駕。稼軒此詞,幾成絕調,便因他能運渾瀚之氣,驅沉鬱之情。
詞寫傷春之懷,卻以情人分釵、桃葉渡江、南浦送別三個意象興起。釵,是兩股簪子合在一起的頭飾,分釵,喻指情人分離。桃葉是晉代王獻之的小妾,嘗渡江,獻之為作《桃葉歌》。南浦則典出《楚辭·九歌·河伯》:「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以別恨興起,使全篇都籠罩在一種幽怨的氣息中。時當暮春,正是雨橫風狂的時節,「 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則心中之哀怨無聊可知。「斷腸片片飛紅」,是說每一片飛花的凋零,都增我斷腸,下一句則說,誰能叫那流鶯討厭的叫聲止住?它只是在聲聲地催促著春天遠離我們。
詞的下片,作者以深閨中思婦自比。她心緒不寧,時時把鬢邊的花摘下來,一瓣一瓣地數著:他會回來,他不回來,他會回來,他不回來……數了又數,戴上又摘下。夜已深了,燈火已暗,她睡在羅帳之內,囈囈地說著夢話:春天啊,你把希望帶給了我,讓我終日愁苦,你現在去到哪裡了呢,幹嗎不把我的希望一起帶走,好讓我再也不要有憂愁?
稼軒自托於香草美人,春天喻指本來頗有恢復之雄心,卻終於意氣消沉的宋孝宗。人生有痛苦,是因為人有希望,絕望並不會讓人痛苦,最讓人痛苦的則是,明知是絕望卻依然抱有微茫的希望。這首詞,沉鬱已極,淒厲已極,便因稼軒始終不肯放棄希望的緣故。
稼軒晚年,外戚韓侂 ( tuō ) 胄掌權,此人一心想建功立業,卻又沒有經世治國之才。他想借起用稼軒樹立個人威望,於是稼軒得以起復,嘉泰三年(1203)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四年,知鎮江,這一年,稼軒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他雖然一心想恢復故土,但深明軍事的他,知道以數十年來缺乏訓練、裝備不足之師,不足以躁進。他打算做長期作戰的準備,不料又因舉薦不當的細故被調離前線,不久再被加以「 好色貪財,淫刑斂聚」 的罪名而罷官。
在鎮江時,稼軒想到南朝劉宋時,宋文帝劉義隆三次北伐均告失利的史實,於是寫了下面這首詞,希望韓侂 胄不要輕舉妄動: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這是一篇詞體的諫疏,雖然不是好詞,但很符合古人「 主文而譎諫」 的傳統。可惜,韓侂 胄並未能聽從他的意見。開禧二年(1206),韓侂 胄倉促北伐,先小勝而後大敗,最終為史彌遠所害,割了他的腦袋向金人求和。
開禧三年(1207),朝廷對稼軒授以兵部侍郎之職,然而他的生命已經快要走到盡頭了。他以身體的原因力辭起復,回到鉛山瓢泉別墅,不久病故。
稼軒一生,並沒有經歷特別的苦難,但悲劇的本質不是苦難——那是慘劇的本質,而是人生願望與命運的激烈衝突,從這個意義上講,稼軒的人生是典型的悲劇人生。其人生願望越強烈,表現在詞中的悲劇情懷、崇高境界,也就越宏大,這是稼軒雄視兩宋、震耀百世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