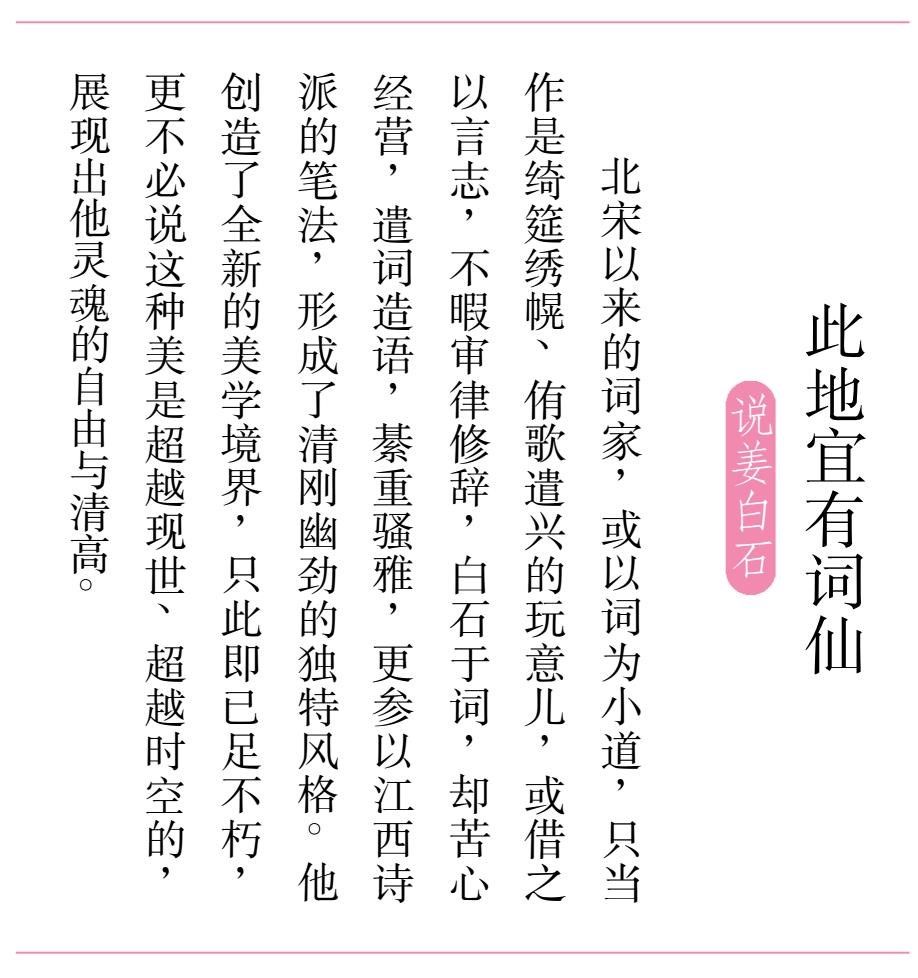

杭州城北,古有東西馬塍( cheng ) ,居民以蒔花為業,南宋名人,多葬於西馬塍。今天東西馬塍俱無陳跡以供多情人憑弔,只有一條馬塍路,繁忙熙攘,兩側高樓林立,儼如森林。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詞人魏新河就每年躑躅在馬塍路上,想尋覓一位南宋大詞人的墓塋。他要找的這位大詞人,姓姜名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是詞學史上極為重要的人物,開創了幽勁清剛的詞風,在婉約、豪放之外,別樹宗派,對後世詞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白石是江西鄱陽人,他的先祖,本來系出甘肅天水,十三世祖姜公輔,已經著籍嶺南道愛州日南縣(今屬越南),曾在唐德宗朝為宰相。七世祖姜泮因任饒州教授,遂遷江西。白石的父親姜噩,中了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以新喻丞知漢陽縣,漢陽,即白石詞中的古沔之地。
白石的人生經歷很簡單,他沒有經歷過乾坤板蕩、宦海浮沉,終其一生,過的是被無產階級學者罵為「 寄生蟲」 的清客生活。其作品或登臨弔古,或睹物懷人,不依門戶,自寫其心,瀟灑中帶著孤高;他的感慨、他的情志,都被巧妙地隱藏在那些氣息淳雅的詞句背後;他的作品的藝術性,無疑比其思想性更突出。這在中國古典作家中,實在是非常異類的。他的詞多以意象組織成篇,不像其他詞人那樣有明顯的理路或情感脈絡,他又通音律,能自度曲,作品遂能超越現世,進入更純粹、更不朽的宇宙,正如南宋末年的大詞人張炎所稱許的那樣:「野雲孤飛,去留無跡。」(《詞源》)
朱庸齋先生指出,白石詞「 以清逸幽艷之筆調,寫一己身世之情」,於豪放婉約之外,別開「 幽勁」 一路;又說:「 詞至白石遂不能總括為婉約與豪放兩派耳。」認為「 白石雖脫胎於稼軒,然具南宋詞之特點,一洗綺羅香澤、脂粉氣息,而成落拓江湖、孤芳自賞之風格。此乃糅合北宋詩風於詞中,故骨格挺健,縱有艷詞,亦無濃烈脂粉氣息,而以清幽出之;至傷時弔古一類,又無粗豪與理究氣味,而以峭勁出之。」(《分春館詞話》卷四) 這是對白石詞的風格及其在詞史上的地位做出的精當評價。但朱先生和清末詞人周濟、陳洵一樣,認為白石脫胎於稼軒,茲說我不能贊同。
周濟的《宋四家詞選》以白石為稼軒附庸,謂「 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為清剛,變馳驟為疏宕,蓋二公皆極熱中,故氣味吻合」 (《宋四家詞選序》) ,指出白石詞風有清剛疏宕之姿,誠為卓識,但謂白石像稼軒一樣極熱中(躁急心熱) ,未免失之已甚。不同於稼軒的霸儒氣質,白石更醉心於營造純粹的靈魂安居所,他對美的追求是超越了道德追求的,這才是白石詞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們且看白石的一篇和稼軒之作《永遇樂·次稼軒北固樓韻》:
雲隔迷樓,苔封很石,人向何處。數騎秋煙,一篙寒汐,千古空來去。使君心在,蒼崖綠嶂,苦被北門留住。有尊中、酒差可飲,大旗盡繡熊虎。前身諸葛,來游此地,數語便酬三顧。樓外冥冥,江皋隱隱,認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長淮金鼓。問當時、依依種柳,至今在否。
迷樓在揚州,為隋煬帝所築,很石在鎮江北固山甘露寺,因其形如羊,故而得名。(很是執扭、不聽從的意思,羊性執扭,故有「很如羊」的說法。) 首三句謂維揚鎮江之地,俱被雲隔苔封,中興名將如稼軒者,久不得到此練兵。「數騎秋煙,一篙寒汐,千古空來去」 三句,是說登樓憑眺,望見騎馬的健兒揚起秋塵,趁著秋日晚潮的船隻,他們的奔忙在歷史上不會留下一點印跡。由此引出「 使君心在,蒼崖綠嶂」,意謂稼軒該對十丈紅塵,久已生厭,當心懷隱逸之志了。我們知道,稼軒是被迫歸隱的,他一直希望能被起用,好到前線指揮恢復中原的事業,何以白石要這樣說他呢?原來,古人的傳統,是以隱逸為高,這是對稼軒的恭維。「苦被北門留住」用《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典:「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 北門,軍事重地的代稱。
過片三句,以諸葛亮比喻稼軒,謂稼軒能致身報國。「 樓外冥冥,江皋隱隱,認得征西路」,是說樓外冥冥的飛鴻,認得那隱隱可見的江岸,正是東晉征西大將軍桓溫經行過的道路,是以桓溫喻稼軒。「中原」 三句,謂淪陷區人民士氣未喪,天天盼著大宋的軍隊自淮水南邊打來。結三句則宕開一筆,用桓溫「 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的著名典故,隱隱感慨稼軒直至晚年,才得見用。
此詞心眷直北遺民,祈望朝廷恢復神州故土之情,固當被稼軒引為同志,但論其氣質,卻與稼軒截然殊途。稼軒原詞的氣質是豪宕不羈的,譬如書法,以佈局氣勢見勝,而點畫或略嫌粗疏,白石卻是法度謹嚴,清剛韶秀,令人觀之忘倦。
再如《漢宮春·次韻稼軒會稽秋風亭觀雨》:
雲曰歸歟。縱垂天曳曳,終反衡廬。揚州十年一夢,俯仰差殊。秦碑越殿,悔舊遊、作計全疏。分付與、高懷老尹,管弦絲竹寧無。知公愛山入剡,若南尋李白,問訊何如。年年雁飛波上,愁亦關予。臨皋領客,向月邊、攜酒攜鱸。今但借、秋風一榻,公歌我亦能書。
稼軒原詞如下:
亭上秋風,記去 年裊裊 ,曾到吾廬 。山河舉目雖異 ,風景非殊 。功成者去 ,覺團扇 、便 與人疏 。吹不斷 、斜 陽依舊 ,茫茫禹跡 都無。千古茂陵 詞在 ,甚 風流章 句,解擬 相如 。只 今木落 江冷 ,眇眇 愁予 。故 人書報 ,莫因循 、忘卻蓴鱸 。誰念 我、新 涼燈火 ,一編太 史公 書。
白石的和作比稼軒多一韻,是《漢宮春》的又一體。不同於稼軒的慷慨沉鬱,白石詞的品格是蕭閒振舉的,他們有著不同的人生態度,自然也有著不同的境界與風格。
又如他少年時得到前輩詩人蕭德藻(號千巖老人) 青賞的這首《揚州慢》:
揚州慢
淳熙丙申正日, 予過 維揚。夜雪 初霽, 薺麥彌望。入其城, 則四顧蕭條,寒水自 碧,暮 色漸起, 戍角悲吟。 予懷愴然, 感慨今 昔, 因自度此曲。千巖 老人 以為有 黍離之 悲也。
淮左 名都,竹 西佳處 ,解鞍 少駐初程 。過春風十里,盡薺麥 青青。自胡 馬、窺 江去 後,廢池喬木 ,猶厭 言兵 。漸黃昏 清角 ,吹寒都在空 城。杜郎俊賞 ,算而今、重到須驚 。縱豆蔻 詞工 ,青樓夢好 ,難賦深 情。二 十四橋仍在 ,波 心蕩、冷 月無聲。念橋 邊紅藥 ,年年知為誰生 。
朱庸齋先生以為「 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 頗似稼軒,實則此詞並無稼軒那樣執著現世、矢志恢復的激越之情,白石的精神世界是超拔的,他不是新中國文學史所推崇的那種現實主義作家。稼軒是儒將本色,出其緒餘為詞,詞是他人生理想的附庸;白石此詞,卻更多的是表達自己內心的直感,傳遞的是心頭淒涼的況味,因此他的詞也就更具獨立價值,更加自由。
白石集中此類作品不多,我推測其原因是,他是一個天生的隱士,對於現實政治並無特別興趣,故他的偶像是唐末隱士陸龜蒙。《點絳唇·丁未冬過吳松作》云:
燕雁 無心,太湖 西畔隨 雲去 。數峰 清苦 。商略黃昏雨 。第四橋 邊,擬共天隨住 。今何許 。憑闌懷古 。殘柳參差舞 。
陸龜蒙號天隨子,「擬共天隨住」就是想追躡陸龜蒙的腳步,歸隱於茲。白石大抵完全無法融入營營汲汲的現實世界,他的理想是追隨天隨子,做一個真的隱士,在山林中逃遁紅塵。
北宋以來的詞家,或以詞為小道,只當作是綺筵繡幌、侑歌遣興的玩意兒,或借之以言志,不暇審律修辭,白石於詞,卻苦心經營,遣詞造語,綦重騷雅,更參以江西詩派的筆法,形成了清剛幽勁的獨特風格。他創造了全新的美學境界,只此即已足不朽,更不必說這種美是超越現世、超越時空的,展現出他靈魂的自由與清高。
白石一生未嘗出仕。他除了賣字以外,就大都靠別人接濟。
白石自幼隨宦漢陽,父親很早過世,他長期依長姊生活於漢川縣。淳熙年間,青年白石在湖南遊歷,結識了福建人蕭德藻。蕭德藻在當時詩名藉甚,一遇白石,即大生知遇之感,感慨地說,我作詩四十年,才遇到一個可以與之談詩之人,遂攜白石至湖州生活,並把自己的侄女嫁給了白石,白石一家的經濟,也完全由他提供。
後來千巖翁又把白石推薦給了名詩人楊萬里,楊萬里更介紹他去拜謁另一位大詩人范成大(號石湖) 。石湖是做過大官的,致仕(退休)後經濟仍非常豐裕,對白石也有厚貺。這期間,白石為作詠梅詞二闋,用仙呂宮定譜,曰《暗香》《疏影》。詞曰:
舊時 月色 。算幾番照 我,梅邊吹笛。喚 起玉 人,不管 清寒與攀摘 。何遜 而今漸老 ,都忘卻 、春風詞筆 。但 怪得、竹外疏 花,香冷 入瑤席 。江國 。正寂寂 。歎 寄與路遙 ,夜雪初積 。翠尊易泣 。紅萼 無言耿 相憶 。長記 曾攜手處 ,千樹壓 、西湖 寒碧 。又片片 、吹盡也,幾時 見得。(《暗香》)
苔 枝綴玉 。有翠禽 小小,枝上同宿 。客裡相逢,籬角黃昏 ,無言自倚修竹 。昭 君不慣胡沙遠 ,但暗憶 、江南 江北 。想佩環 、月夜歸來 ,化 作此花幽 獨。猶記深宮舊 事,那 人正睡 裡,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 ,早 與安排 金屋 。還 教一片隨波去 ,又卻 怨、玉龍哀 曲。等 恁時 、重覓幽 香,已入小窗橫幅 。(《疏影》)
二詞作於宋光宗紹熙二年辛亥(1191)之冬,作曲填詞,白石一身任之。這兩首詞,自清代以來,有很多學者認為是有寄托的作品,周濟至謂白石「 唯《暗香》《疏影》二詞,寄意題外,包蘊無窮,可與稼軒伯仲」 (《介存齋論詞雜著》) ,其《宋四家詞選》評《暗香》,謂有一朝盛衰之慨,又謂《疏影》以「 相逢」「 化作」「莫似」 為骨,於國是「 不能挽留,聽其自為盛衰」 ;龍榆生先生認為《暗香》是詞人希望石湖能愛惜人才,設法對自己加以引薦(《詞學十講》) ;《疏影》一詞,張惠言謂是「 以二帝之憤發之」 (《詞選》),鄧廷楨《雙硯齋詞話》、鄭文焯《鄭校白石道人歌曲》均認為,《疏影》是抒寫對相從徽、欽二帝被擄北上的后妃的同情。
我以前亦相信這兩首詞是寄托之作,拙著《大學詩詞寫作教程》前三版均依此解說,但近年已盡拋成說。因細按詞前小序,有「 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肆習之,音節諧婉」 之語,音樂風格不像是有寄托的,如果真是寄托之作,以白石之邃於音律,音節應該淒婉哀涼才對。
我認為,這兩首詞是單純的詠物之作,是兩件純粹的藝術品,它們的用意只是為了禮讚梅花,傳遞美、再造美,沒有除此以外的別的目的。詞人把與梅花相關的典故、詩句臚列編排,串珠成鏈,再加以適當的想像,顯得詞的全首像是有完整的敘事脈絡,實則不過是詞人的技法高明,令人不覺其湊泊而已。
白石的金閶(蘇州的古稱) 之行,除了獲得范成大的資助,還獲贈一慧婢名曰小紅。這一年的除夕,白石意氣風發,帶著小紅回湖州,船過垂虹橋,作有一絕:「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小紅有著不俗的藝術造詣,與白石主僕情深,甚是相得,後來年長嫁人。白石身歿後,友人蘇泂 挽之以詩,有「 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 之語,可以想像,小紅是一位與之精神高度契合的膩友。
當時如石湖這樣賞識白石的名公巨儒不在少數。宋末周密曾偶得白石手跡一份,是白石自道其身世的書信。信中列數說,「內翰梁公,於某為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為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為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為子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為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為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文,又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翬 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者。」白石的藝術才華是多方面的,他既長於詩詞,又擅駢散文章,同時又對禮樂有深湛之研究,著有專書,書法得人愛賞,其人品氣質更是清雅脫俗,似晉宋(南朝劉宋) 之間的雅士,他的廣受歡迎,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過,被那麼多的權貴名公賞識,並沒有改變白石「 窶困無聊」 的境遇,這大抵是因為白石心性清高,絕不會主動說出干謁求進的話來。唯有南宋大將張俊的曾孫張鑒字平甫者,主動資助白石,歷十年之久,與白石情甚骨肉。
張平甫因白石累試不第,擬出資為白石捐官,以白石的清高,當然辭謝不敏。白石曾力圖自正途謀求朝廷出身:寧宗慶元三年(1197),向朝廷進大樂議及琴瑟考古圖,時太常嫉其能,不獲盡其所議,五年(1199),又上聖宋鐃歌十二章,皇帝下詔讓他不必經過地方的初試,直接參加禮部試,又不第,遂以布衣終。
平甫又欲割無錫的良田贈給白石,白石也一樣拒絕了。何以白石寧願一直接受平甫的資助,卻不肯接受永久的產業呢?原來,南宋之時,大官僚養士之風盛行,稼軒亦嘗因劉過的一首詞,而厚貺之二十萬錢之巨。蓋當時風氣如此,貺者不以為惠,受者不以為異。白石接受蕭千巖、范石湖、張平甫的資助和一些特殊的饋贈,這都不是問題,白石亦報之以「 竭誠盡力,憂樂關念」,但接受良田,性質便完全不同了,那是接受了產業,所謂無功不受祿,白石要做的是清高的卿客,而不是受祿的家臣,他的選擇決定了他能終身葆有心靈的自由。
張平甫去世後,白石的十年門客生涯也走到了盡頭,他在經濟上開始陷入困頓,只能在浙東、嘉興、金陵間旅食。「旅食」 這個詞說得是比較文雅的了,不太好聽的說法則是打秋風。白石先有三子早夭,歿時兒子薑瓊才十七歲,無力營葬,幸得友人吳潛等人謀為營葬於杭州之西馬塍。倘若有誰為白石撰寫墓誌銘,應該用上與他同在蕭千巖門下學詩的另一位白石黃白石(黃景說,字巖老) 的話:「造物者不欲以富貴浼堯章,使之聲名焜 耀於無窮也!」
白石墓至清代尚存。時至今日,東西馬塍早已全無蹤影,更不必說白石的墓塋了。據《湖墅小志》:「東西馬塍在溜水橋以北,以河為界,河東抵北關外東馬塍,河西自上下泥橋至西隱橋為西馬塍。錢王時蓄馬於此,故以名塍。」然則今天我們的馬塍路,不過借古地名而命名,與宋時恍如花海的東西馬塍,沒一點關係。詩人王翼奇就居住在馬塍路附近,他多年尋訪白石墓不得,只好把他居住的小區中心花園聊當白石的厝室,恭默祭拜。那一年,杜鵑開得正盛,同樣久覓白石厝室不得的詞人魏新河過訪,填了一首《竹枝》贈之:「欲把詞心托杜鵑。群花不語樹無言。翠禽小小來還去,過了梅花八百年。」不久,魏新河便在《白石詩集》中讀到「山色最憐秦望綠,野花只作晉時紅」 之句,詩後有白石自註:「右軍祠堂有杜鵑花兩株,極照灼。」他想到,與王羲之(曾為會稽內史領右將軍,故稱王右軍) 心靈異代相通的白石,也許會選擇同樣長眠於杜鵑花下,只要誠爇( ruo ) 心香,又何妨今之馬塍路不是古之東西馬塍,今之杜鵑,不是八百年前的杜鵑呢?
宋代陳郁《藏一話腴》載:白石氣質相貌十分溫弱,彷彿連衣服的重量都承受不住,沒有立錐之地的田產,自己過的是清客生涯,卻還每天養著食客,收藏的圖書字畫,更是一筆不菲的財富。這樣的奇跡,只能出現在經濟高度發達、文化發展到極致的南宋。
在世俗的眼中,白石所擅長的文章詩詞、書法音樂,沒有一樣是「 有用的」,都是徹底的「 為己」 之學。正常情況下,一個像白石一樣的人,如果不肯犧牲自己的獨立精神、自由意志,這些才華幾乎不能為他換取任何現實利益,白石幸運地生活在中國文化的巔峰時代,有蕭德藻、范成大、張鑒這些既有經濟實力又有極高鑒賞力的人賞識他,因此不需要諂媚取容、降志辱身,就能維持著有尊嚴的生活。
白石詞,沒有一絲一毫的世俗味,是雅詞的極則,這與他不汲汲於功名利祿,而終身追求心靈的逍遙自適有莫大關係。他的白石道人之號,是友人潘檉所贈,大概潘檉早就發現了他超拔出塵的精神特質。明以後的學者,誤把宋末元初杭州人姜石帚當作白石的別號,故常稱白石為石帚老仙,其事雖誤,但以「 仙」字冠在白石頭上,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翠樓吟》詞有「 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 之語,詞仙正是他的心靈自許。
當時的文化環境保證了白石可以過上在較長時間內不必營營汲汲的生活,保證了他可以不縈心俗務,而專力於純粹藝術的創造,這才有了這位卓然於文化史上的詞仙,這才有了他「 野雲孤飛,去留無跡」 的高卓詞品。那些資助白石的大官僚,如果他們做的是一項投資,得說這是一項回報率極高的投資,因為他們用有限的金錢,換來的是高聳入雲、萬古屹立的文化奇峰。
在儒家而言,人生的終極價值,固然在於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事業;而自莊子觀之,則逍遙之境,才是人生的終極理想。然而人生在世,衣食住行,莫不需要經濟的支撐。原始人的幾乎全部生命,都用來尋找食物,當然沒有逍遙可言,今天科學昌明,物質進步,而人類俯仰於世,熙來攘往,無不為房子、車子、票子而苦惱,心靈的不自由,與原始人也沒有多大分別。文化的傳承卻需要有一批脫心俗諦、專心研習的人。中國古代因孔子之教,士大夫戮力王事,一面獲取朝廷俸祿,一面傳承文化,而像白石這樣,未得因科舉入仕而解決衣食問題,但能靠知音者的周濟,得以專力藝術創造,也是一種不壞的選擇。也正因有當時的養士之風,南宋文化才能處在一個特別高的高度之上。
其實,養士之風不獨中國為然,歐洲的情形也是一樣。啟蒙運動時期,歐洲很多的文學家、藝術家,都曾受過貴族尤其是貴婦人的供養。比如俄羅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就有一位梅剋夫人定期給他寄去數額不小的生活補貼,而他們一輩子唯一的一次見面是在意大利,梅剋夫人偶然散步經過了柴可夫斯基的旅館,而後者正好走到陽台上,他們的目光互相注視了一下,此後再未見面。
同柴可夫斯基或其他被貴族資助的歐洲文學家、藝術家一樣,白石雖然靠友人的接濟生活,但他的人格是偉岸的,精神是自由的,所以才能寫出那些超拔的、穿透歷史的詞作。
最後談一談白石的愛情詞。
今人夏承燾先生推斷,白石在青年時,曾經愛眷合肥勾欄中的一對姊妹,這對姊妹妙解音律,一擅琵琶,一擅彈箏,這一段感情,維繫時間既久,早就昇華為一種柏拉圖之戀,時過二十年,白石還常時時魂牽夢縈,詞集中與合肥情史有關的竟達二十首,佔他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
一萼紅
丙午人日, 予客長 沙別駕之觀 政堂。 堂下曲 沼, 沼西 負古垣,有 盧橘幽篁,一 徑深曲。 穿徑而 南, 官梅數十 株, 如椒、 如菽, 或紅 破白露,枝 影扶疏。 著屐蒼 苔細石間, 野興橫生, 亟命駕登定王台。 亂湘流、入 麓山, 湘雲 低昂, 湘波容與。 興盡 悲來, 醉吟成 調。
古 城陰 。有官 梅幾許 ,紅萼 未宜簪 。池面冰膠 ,牆 腰雪老 ,雲意還又沉沉 。翠籐共 、閒穿徑竹 ,漸笑語 、驚 起臥沙禽 。野老 林泉 ,故王台榭 ,呼喚登 臨。南去北來 何事,蕩湘 雲楚 水,目極傷 心。朱戶粘雞 ,金盤簇燕 ,空歎時 序侵尋 。記 曾共 、西樓雅 集,想垂楊 、還裊 萬絲 金。待 得歸鞍到時 ,只怕 春深 。
此詞作年,約當白石三十二歲時。夏承燾先生認為,當是白石集中關涉合肥情史最早的一篇。
首三句,是說官梅(政府所種的梅) 扶疏於古城之陰,紅萼將放,還不適宜簪在鬢上,寫出了梅的孤高之態。「池面」 三句,則謂觀政堂下曲沼冰凍未化,古城垣的牆腰之上,粘著一些將化未化的殘雪,天氣沉陰,不知何時雲開日出。「翠籐共」 以下,直至上片結束,則寫詞人拉著人一起探幽尋勝的興致。
過片直抒胸臆,謂羈旅生涯,未知何時是了局。「朱戶粘雞,金盤簇燕」 點明人日風俗,古人在人日這一天,會用彩色的紙或金箔剪成人和動物的形狀,有的插在頭上,有的放在盤子裡,有的粘在窗戶上、屏風上。「空歎時序侵尋」 是說時光荏苒,依舊天涯孤旅。「記曾共、西樓雅集,想垂楊、還裊萬絲金」 連用兩句尖頭句,句法參差跌宕,寫出對佳人的深切思戀。夏承燾先生認為,凡是白石詞中出現梅、柳意象的,多與合肥情事有關。柳枝初芽未綻,是金黃色的,故謂之金縷,這兩句的意思是,還記得上次我們在西樓雅集,而這個時候正好是垂楊初芽,彷彿是萬絲金縷隨風裊娜的初春啊!結句則是說,等我們再次相見,不知要到什麼時候。由初春到春深,本來只有兩個月的時間,但詞的獨特體性決定了它不能像詩一樣,用「百年」「 萬里」等宏大意象,而以「 只怕春深」 作結,便已見相思之酷了。
白石在《解連環》一詞中,記述了與這對姊妹一見傾心的感覺。她們有著高超的藝術:「大喬能撥春風,小喬妙移箏,雁啼秋水」 ;初會面時,只是隨意地打扮了一下,卻不掩其動人的顏色:「柳怯雲松,更何必、十分梳洗」 ;只一句話就勾住了詞人的心:「道『 郎攜羽扇,那日隔簾,半面曾記』。」勾欄女子,深深明白男性的心理,也就難怪白石會眷眷不忘了。
小重山令·賦潭州紅梅
人繞湘 皋月墜時 。斜橫 花樹小、浸 愁漪 。一春幽 事有誰知 。東風冷 ,香遠茜裙 歸。鷗去昔游非 。遙 憐花可可、夢依依 。九疑 雲杳斷魂啼 。相思血,都沁 綠筠 枝。
潭州就是今天的長沙。詞人深諳詠物詞的做法,他要詠的,不但是紅梅,還是湘中潭州的紅梅,故先以「 茜裙歸」 比喻紅梅的開放,又以大舜崩於瀟湘蒼梧之野、葬於九疑山上,其二妃娥皇、女英終日悲啼,淚濺竹枝,沁成竹斑,遂名湘妃竹的故事,把紅梅在枝頭綻放比喻成是相思血沁入竹枝。但細玩詞意,懷人之意還是十分顯豁的,詞中明顯有一個「我」在,與一般詠物之作不同。
首句「 人繞湘皋月墜時」,畫面感濃烈,意謂詞人繞著湘水岸邊徘徊,不覺月亮將沉,又將黎明。詞人還怕讀者不明他的心跡,以「 斜橫花樹小、浸愁漪」 表明,這不是一篇單純的詠物之作。這兩句是說斜生橫出的梅樹,長得很玲瓏,月光下花樹的影子映在湘水之上,泛著令人愁苦的漣漪。「一春幽事有誰知」是說整個春天過去,在湘江岸邊曾發生了什麼幽情別恨,沒有人知道。「東風冷,香遠茜裙歸」 是說春寒尚自料峭,空氣中已經有了梅花淡遠的清香,彷彿是身著茜紅色裙子的佳人歸來。
「 鷗去昔游非」本是用《列子》中的典故:從前海邊有個人喜歡鷗鳥,每天清晨到海邊和鷗鳥玩,那些翔而後集陪他玩耍的鷗鳥何止百數!他的父親知道後,就跟他說,下次你捉一隻鷗鳥給我玩吧。第二天他再去海邊,因為心中有了機心,鷗鳥就在天上飛舞,不再下來了。這裡,詞人是懺悔未能勇敢地決定與愛侶長相廝守,只能在思念中咀嚼痛苦。「九疑」 以下,是說潭州紅梅就像娥皇、女英的相思淚滴盡,眼枯見血,沁在綠竹枝上。很顯然,娥皇、女英正是指合肥姊妹。
江梅引
丙辰之 冬, 予留 梁溪,將 詣淮南不得, 因夢思 以述志。
人間離別易 多時 。見梅枝。忽 相思。幾 度小窗 袁 幽夢手同攜 。今夜夢 中無覓處 ,漫徘徊 。寒侵被 、尚未知 。濕 紅恨墨淺 封題 。寶箏空 ,無雁 飛。俊游 巷陌 ,算空 有、古木斜暉 。舊 約扁舟 ,心事已成非 。歌罷淮南 春草賦 ,又萋萋 。漂零 客、淚滿衣 。
梁溪是江蘇無錫,詞人羈留無錫,不得赴合肥與愛侶相會,遂作此詞見意。此詞劈頭一句「 人間離別易多時」,悵惋之情,明白說出,承以「 見梅枝。忽相思」,更覺神完氣足。接下來是記述夢中情景:「幾度小窗,幽夢手同攜。」然而夢中情事,不是人想要有便有的,今夜夢中就全然無法與她相會,只好在夢境裡隨意徘徊,夜深寒重,尚不肯醒來。
「 濕紅恨墨淺封題」 一句轉為寫對方。「濕紅」 指女子的情淚;「 淺封題」 是說漫然地把書信封好並題款,「 淺」字寫出女子思人慵懶無聊的情態。「寶箏空,無雁飛」是說擅於彈箏的那位愛侶,連奏曲的心情也沒有了。箏上的柱子如雁斜行,故名雁柱,「無雁飛」就是沒有人彈奏它,這是一種拈連的修辭寫法。詞人追想少年時給自己留下無限快樂和溫馨的淮南巷陌,而今只有參天的古木映照著斜陽。「舊約扁舟,心事已成非」用越大夫范蠡功成身退,帶著西施泛舟五湖(太湖的別稱) 之典,意思是他跟這一對姐妹,當年有婚嫁之約、偕隱之志,可是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歌罷淮南春草賦」 語帶雙關,既是指漢代淮南小山的《招隱士》,也實指合肥之地。《招隱士》是一篇辭賦,中有「 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這一名句,後來但凡作詩填詞,只要用到王孫、春草、芳草、萋萋等字,皆謂離別。結句「 漂零客、淚滿衣」,同樣濃墨重筆,可以想像,倘使小紅歌之,必當發音淒斷,令聽者沾衣了。
白石詞數度睹梅而思其人,以至於我懷疑這對姐妹其中一位名字裡有個梅字。
白石的很多詞都有小序,此舉頗遭周濟指摘。《介存齋論詞雜著》以為,「白石好為小序,序即是詞,詞仍是序,反覆再觀,如同嚼蠟矣。詞序、序作詞緣起以此意詞中未備也。今人論院本,尚知曲白相生,不許復沓,而獨津津於白石詞序,一何可笑。」但夏承燾先生認為,白石的很多情詞之所以要加題序,是因為他要在題序中亂以他辭,故為迷離,「此見其孤往之懷有不見諒於人而宛轉不能自已者」。當時的婚姻所憑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白石銜千巖翁賞遇之恩,娶了其侄女,對妻子有一份道義之責,但對於少年時自由戀愛上的女子,則久懷不忘,其情必不能見容於其妻,這才有了小序的「 亂以他辭」。
浣溪沙
予女須家沔之山陽, 左白 湖, 右雲 夢,春水 方生, 浸數千里, 冬寒 沙露, 衰草入雲。 丙午之秋, 予與 安甥或蕩 舟採菱, 或舉火罝 兔, 或觀 魚塞 下,山 行野吟,自 適其 適, 憑虛悵望, 因賦是 闋。
著酒行行滿袂 風。草枯 霜鶻落 晴空 。銷魂 都在 夕陽中。恨 入四弦 人欲老 ,夢尋 千驛意難通 。當時 何似莫匆匆。
女須本來是屈原的姐姐的名字,這裡是指白石的長姊。小序的大意是說,長姊家所居的漢陽地區山陽縣,處於白湖雲夢二澤之間,四時風景佳勝,白石和長姊的兒子安徜徉山水之中,非常逍遙適意,詞人卻「憑虛悵望」,一個「悵」字微露心跡。
詞的上片,寫詞人帶著些微酒意,在秋野中走啊走,秋風吹來,兩袖鼓蕩。野草枯黃,野兔之類的小動物難以隱藏形跡,霜天之上的蒼鶻就猛地直衝而下,意圖攫取。這一句是化用了老杜「 草枯鷹眼疾」 的詩意,但煉一「 落」字,非常傳神。夕陽西下,詞人不禁感慨時光流逝,居然與愛人分別了那麼久,心頭自有一種說不出的帶有憂傷,又帶有甜蜜的感覺,那便是銷魂的滋味。清代詞人納蘭性德,其《浣溪沙·西郊馮氏園看海棠因憶香嚴詞有感》:「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經年。一片暈紅才著雨,幾絲柔綠乍和煙。倩魂銷盡夕陽前。」結句渾學白石的「 銷魂都在夕陽中」,而並未擅出藍之勝。
過片,詞人想起了擅彈琵琶的那個她(琵琶是四弦) 袁 相信別後她也是一般的幽愁別恨,彈奏琵琶時,一定在惋歎聚日無多,人卻漸漸地老去,詞人在夢裡歷遍萬層山、千重驛,卻無法真的把自己的相思傳遞過去。結句「 當時何似莫匆匆」,情感不再婉曲含蘊,而是直截凝重:早知今日恁般相思,當初何必要那麼匆忙離去呢?這種直截凝重的寫法,需要極其濃摯的情感,白石的詞一向是舂容和雅的,但偶一用重拙之筆,便尤其驚心動魄。
對於這一句,民國女詞人呂碧城深愛賞之,直接用到了自己的詞裡:「殘雪皚皚曉日紅。寒山顏色舊時同。斷魂何處問飛蓬。地轉天旋千萬劫,人間只此一回逢。當時何似莫匆匆。」相對於原作的深婉清華,呂碧城的仿作未免有些一洩無遺,了無餘致了。
白石追念合肥情事的作品,我最喜歡的是以下二首:
踏莎行
自沔東來,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夢而作
燕燕輕盈 ,鶯鶯嬌軟 。分明又 向華胥 見。夜長爭 得薄 情知 ,春初早被 相思染 。別 後書辭 ,別時針線 。離魂暗逐郎行遠 。淮南皓 月冷 千山,冥冥 歸去 無人管 。
鷓鴣天·元夕有所夢
肥 水東流無盡期 。當初 不合 種相思。夢 中未比 丹青見,暗 裡忽驚 山鳥啼 。春未綠,鬢先絲 。人間別久 不成悲 。誰 教歲歲 紅蓮夜,兩處沈吟各 自知 。
第一首詞作於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詞人自漢陽順江流而東,諒曾在合肥盤桓,江上感夢,當系遁詞,所謂的夢境,應該是實有其事。
詞的開頭兩句,是說合肥姊妹體態輕盈,情態嬌軟,二句是互文的手法。(所謂互文,就是要表達燕燕鶯鶯輕盈嬌軟,卻因為對仗的關係寫成「 燕燕輕盈,鶯鶯嬌軟」。又如秦時明月漢時關,實際意思是秦漢時明月秦漢時關,也是互文。) 「 分明又向華胥見」,華胥國是夢境的別稱,但這裡其實是說,再次重逢,彷彿就像在夢裡一樣。「夜長爭得薄情知」是詞人的懺悔,意思是,我真是負心薄倖,你們長夜不眠地思念我,我竟然不知道;「 春初早被相思染」 是情深之極的奇語,本來春深之時,花繁葉綠,色彩絢爛,才更像是相思的濃郁,可是詞人卻說「 春初早被相思染」,初春的一脈新綠,一點鵝黃,都早相思染就,那麼整個春天的色彩,都凝結著濃重的相思,還需要說嗎?
過片三句極寫合肥姊妹的深情。別後書信不斷傾訴相思,別時為詞人密密縫製了春衣,這還不算,更要學唐傳奇中的張倩娘,魂魄離體,跟隨愛郎王宙上京。然而,詞人自有妻室,合肥姊妹不能長自相隨,她們的倩魂,也只好乘著月色冥冥歸去淮南。這樣的結尾,寫盡了詞人悵惘不甘之情,故而成為名雋。
不同於第一首詞的迷離徜恍,閃爍其詞,第二首詞的情感顯得直率奔放,濃烈熾熱。按照夏承燾先生的考證,白石寫這首詞時,已經四十餘歲,距與合肥姊妹初見,已過去二十多年。想來白石的妻子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白石對這一對姊妹的愛情,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這一對姊妹早已離開合肥嫁人,白石再也沒有機會與她們相見了,這才令白石填詞時,少了以前的顧忌。
「 肥水東流無盡期。當初不合種相思」,開頭兩句情感就充沛已極,意謂肥水東流無盡時,詞人對愛侶的相思也沒有盡時。「不合」 是不該、不應當的意思,詞人是在懺悔自己的多情嗎?否。詞人不是在懺悔,而是在默然承受失去愛侶的痛苦。「夢中未比丹青見,暗裡忽驚山鳥啼」,是說今夜終於和她們在夢中相見,可是夢中見到她們的形容,一點也不似畫像那樣真切明晰,不知從哪裡傳來山鳥的啼叫,把詞人從夢中驚醒了。
過片「 春未綠,鬢先絲」 六字沉鬱有力,承元夕(正月十五)的時令寫來,謂時方早春,草樹都未出芽,但兩鬢卻因相思慮煎,早已有了白絲。「人間別久不成悲」 一句,更是驚心動魄之語。只有經歷過相思失意之人,才會真正理解這句話。時光看上去會療治痛苦悲傷,但其實只是把痛苦悲傷給包藏起來,讓人變得麻木了,痛苦悲傷依然還在,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存在罷了。結二句寫得神光離合,堪稱白石的詞中至境。「紅蓮夜」 是指點綴著紅蓮狀綵燈的元夕之夜,白石必定曾與合肥姊妹有過同游燈海的共同記憶。是誰讓我們在每年的元夕花燈之夜,只能兩處思念,卻終於無法廝守?難道是造物主嗎?沉吟,是自有無限心事,卻什麼話也不說出來,短暫的歡娛、恆久的相思,在元夕紅蓮燈點燃的那一剎那,都化成了三人心頭的悸動。
夏承燾先生談到他考證白石的合肥情史,說了這樣的話:「不以予說為然者,謂予說將貶低姜詞之思想內容。然情實具在,欲全面瞭解姜詞,何可忽此?況白石誠摯之態度,純似友情,不類狎妓,在唐宋情詞中最為突出,又何必諱耶?」 白石對合肥姊妹的情感,早就昇華為精神的愛戀,這是我們讀了他的一系列情詞,不得不為之感動的根源。
